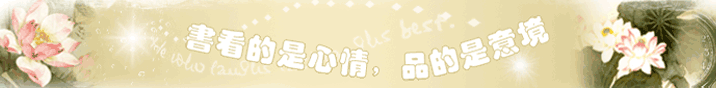一百一十一 今文經學已經失敗了
更新時間:2025-02-01 作者:御炎
我不是袁術 一百一十一 今文經學已經失敗了
這樣的情況發生之后,別說袁樹覺得搞笑,楊賜、張濟那邊也覺得難以接受。 他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自己居然會拉跨到這個地步。 他們安排出擊的雖然不是身邊最值得信任的高才弟子,但也不是門生這種沒有親自傳授本領的大路貨,都是些受到過親自點撥的弟子,平常也都顯得人五人六,一些抽查檢驗,他們也都能通過。 怎么這個時候卻露了怯?如此拉跨? 而且,僅僅只是辯論戰敗倒還好說,但是敗給了袁樹,甚至是敗給了袁樹的弟子們,連袁樹的面都碰不到,這就丟人丟大發了。 堂堂官學,在大漢擁有不可置疑的學術統治力,卻在面對一個新成立三年多的學派面前大敗虧輸,毫無招架之力。 正統學術居然會輸給歪理邪說、旁門左道? 大漢朝廷就是被你們這樣的一群人所代表嗎? 就是你們這樣一群人在負責治國嗎? 袁樹沒有公開明確的表達這樣的觀點,沒有明確的向今文學派開炮,現在還不到時候,但是今文學派自己的拉跨是掩飾不了的。 他們甚至斗不過袁樹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弟子門生們! 袁樹沒有刻意針對,甚至沒有煽動眾人情緒去反擊這些曾經攻擊過自己的人,沒有公開說他們一句壞話。 但是事實勝于雄辯。 袁樹的弟子門生們獲得接二連三的勝利,而那些太學博士、天下名士們的弟子門生則是大敗虧輸,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多了,雒陽城內的輿論就更加徹底的轉變了。 他們開始懷疑自己原先認為高高在上、學究天人的那群人到底有沒有真本領,開始懷疑他們到底是靠著什么身居高位,開始懷疑他們所說的一切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懷疑開始了,且一發不可收拾。 原先觀望的人們開始不斷向袁樹和一心會靠攏,越來越多的人前往報名申請加入一心會,他們似乎都在心底里把袁樹當作了這一次輿論風波的勝利者,已經開始向勝利者靠攏了。 楊賜、張濟、勛奇等人發現局勢越變越差,他們不僅沒有試探出袁樹的知識邊界,反倒把他們自己遼闊的知識盲區暴露給袁樹了。 其他人是什么心態,楊賜不知道,但是楊賜知道的是,他自己已經有點繃不住、輸不起了。 繼續這樣下去,別說議和,他這個帝師的身份能不能維持下去都不一定了。 難道,他也要以帝師之尊親自下場和袁樹辯駁? 萬一輸了,那不就廢了? 教導天子讀書的天下名士居然連他們口中侍讀都不配做的一介小兒打敗了。 楊賜不能接受這種局面。 也絕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他只能派出他最有能力的一批弟子前往向袁樹發起挑戰。 其余眾人也紛紛派遣他們最后的希望前往挑戰袁樹。 于是,在建寧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時候,袁樹率領麾下十三大將與楊賜等人的四十六名最強弟子展開巔峰對決。 他們以春秋和尚書為主要戰場展開激戰,于太學正門口的大廣場上,在數萬人的圍觀之下一戰到底。 此番對決有不少朝廷官員、達官顯貴,乃至于內廷宦官都前來觀看。 雒陽城里的各方勢力都十分關注這場分量極重的對決。 不少人心里都清楚,要是這些代表官學勢力高端戰斗力的精英們被袁樹擊敗了,官學勢力要想挽回局勢,就必須要出動真正的大佬們與袁樹正面對決。 否則,他們以后還怎么在太學里廝混? 袁樹當然沒有一開始就親自下場,而是先讓自己的十三大將們與之對戰,雙方激戰一個時辰,袁樹折損八名大將,而對方已經折損三十九人。 最后剩下的程立、魏甲和蘇初三人繼續對抗對方剩下的七人,又是一輪大戰,兩炷香時間過后,袁樹這邊只剩下魏甲一人,對方還剩三人。 于是魏甲一挑三,在袁樹的注視下爆發全部的能量,將對面三人一頓炮轟,戰至最后,還是倒下了。 最終以毫厘之差擊敗了魏甲的人,是楊賜的得意弟子、徐州東海人王朗。 于是王朗也成為了這一次巔峰對決中唯一一個能和袁樹面對面抗衡的人。 袁樹對他也很感興趣。 不知道為什么,得知面前這人是徐州人王朗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很想對他喊一句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看看他會不會大怒之下當場去世。 他覺得要是有這種可能的話,倒也不必麻煩諸葛亮了。不過王朗倒也不是這種人就是了,諸葛亮不曾罵過他,他也沒有被氣死,相反,他被認為是寬厚的長者。 他是什么人,袁樹不是很感興趣。 讓他感興趣的是,王朗面見他之后,似乎并沒有想要辯駁的想法,而是向他提了一個問題。 “袁君,我想知道,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真的可以拯救時局嗎?真的人人皆可成圣賢嗎?您為何如此肯定?如果做不到,又該如何?” 袁樹有些驚訝。 “好不容易走到這里,不與我辯經,卻要向我提問?” 王朗點了點頭。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您的對手,一定要辯經的話,一定會輸,這是毋庸置疑的,與其做一定沒有意義的事情,不如用這個時間向您請教心中困惑,我不知道如何解答,希望得到您的指點。” 望著面前年輕的“王司徒”那誠懇的眼神,袁樹想了想,緩緩點了點頭。 “你有困惑,那我就為你解答好了。” 袁樹邀請王朗坐下,整頓了一下衣冠。 “挽救時局,我相信是可以的,我不認為做不到,因為如果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我該如何說服眾人與我一起前行呢?” 王朗連忙追問。 “那如果辦不到呢?” “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袁樹笑著搖了搖頭:“關鍵不是能不能成功,因為能不能成功,并非是人力可以預測的,孔子推行儒學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學說能在數百年之后大行其道嗎?他不知道。 他活著的時候周游列國,前往各國推廣自己的學說,卻沒有幾個國家愿意接納他,沒有幾個國家愿意接受他的理念,他屢屢碰壁,直到最后也沒有見到自己克己復禮的理想成功實現。 但是他退縮了嗎?他或許會失望,卻從未退縮,一直都在堅持,不論是否有人愿意相信,有人愿意實踐,他從未退縮過,始終如一,這是他能夠成為當下吾輩眼中圣賢的重要緣由。 圣賢,并不一定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圣賢不會在沒有實現自己的主張的時候就去懷疑這條路是否可行,哪怕是一條死路,圣賢也會走到頭,看到盡頭之后,再作出改變。 所以我認為,我不會改變也不會懷疑我的學說,如果有人認為我是對的,要追隨我,那我歡迎,有人覺得我是錯的,不追隨我,我也接受,但是,我決不允許有人在我沒有付諸實踐之前就斷言我必然失敗。 沒有實踐過的事情,如何能算是失敗?沒有實踐過的學說,怎么就是歪理邪說、旁門左道?沒人知道,之所以有人說,是因為他們心術不正,他們的心臟了,所以看到什么都覺得是臟的。 而對于一個求學之人來說,保持心的純凈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信念的堅定是必需的,沒有這兩點,結果就和那些奸佞小人一樣,為世人所不齒,所以我的學說才是心學。” 王朗聽后,默默思考,緩緩點頭,似有所悟。 少頃,他又抬起頭看著袁樹。 “所以,您反對今文經學而提出自己的學說,是覺得今文經學已經失敗了?” “對,失敗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失敗了。” 袁樹搖頭道:“現在活著的,不過是借尸還魂的神鬼之說罷了,只顧抬頭望天,不去低頭看地,這種飄在空中的學說,如何能讓腳踏實地的人獲得幸福的生活呢?” “可當下的大漢國勢,真的如同您所說的那樣,已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王朗疑惑道:“如果已然如此,當下的情況應該更加兇險才是,應該早就混亂不堪了才是。”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袁樹嘆息道:“昔日文王已經得到三分之二的諸侯的聯合,卻依然對紂王稱臣,認為時機不對,不能伐紂,一直等到武王即位,才終于伐紂成功,這不是因為文王畏懼紂王,而是因為萬事萬物的演變需要時間。 莊稼不能一天長成,一個國家,無論多么的腐朽墮落,也不會在一瞬間就崩潰,當它出現崩潰的前兆的時候,往往還會堅持很長時間才會走上真正的末路,在此期間,并不會使得所有人都認為它將要崩塌。” 王朗一愣。 “您……認為大漢江山將要崩塌嗎?” “如果沒有人可以挽救大漢,那么大漢的崩塌并不是不可能的。” 袁樹嘆息道:“王君,大漢外有鮮卑、匈奴,內有災荒、流民,官員貪腐不知凡幾,執掌權柄者皆短視,只為自己,不為國家,地方豪強兼并土地,掠奪平民,造孽無數,此情此景,王君不覺得熟悉嗎?” (本章完) 我不是袁術 一百一十一 今文經學已經失敗了
這樣的情況發生之后,別說袁樹覺得搞笑,楊賜、張濟那邊也覺得難以接受。 他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自己居然會拉跨到這個地步。 他們安排出擊的雖然不是身邊最值得信任的高才弟子,但也不是門生這種沒有親自傳授本領的大路貨,都是些受到過親自點撥的弟子,平常也都顯得人五人六,一些抽查檢驗,他們也都能通過。 怎么這個時候卻露了怯?如此拉跨? 而且,僅僅只是辯論戰敗倒還好說,但是敗給了袁樹,甚至是敗給了袁樹的弟子們,連袁樹的面都碰不到,這就丟人丟大發了。 堂堂官學,在大漢擁有不可置疑的學術統治力,卻在面對一個新成立三年多的學派面前大敗虧輸,毫無招架之力。 正統學術居然會輸給歪理邪說、旁門左道? 大漢朝廷就是被你們這樣的一群人所代表嗎? 就是你們這樣一群人在負責治國嗎? 袁樹沒有公開明確的表達這樣的觀點,沒有明確的向今文學派開炮,現在還不到時候,但是今文學派自己的拉跨是掩飾不了的。 他們甚至斗不過袁樹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弟子門生們! 袁樹沒有刻意針對,甚至沒有煽動眾人情緒去反擊這些曾經攻擊過自己的人,沒有公開說他們一句壞話。 但是事實勝于雄辯。 袁樹的弟子門生們獲得接二連三的勝利,而那些太學博士、天下名士們的弟子門生則是大敗虧輸,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多了,雒陽城內的輿論就更加徹底的轉變了。 他們開始懷疑自己原先認為高高在上、學究天人的那群人到底有沒有真本領,開始懷疑他們到底是靠著什么身居高位,開始懷疑他們所說的一切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懷疑開始了,且一發不可收拾。 原先觀望的人們開始不斷向袁樹和一心會靠攏,越來越多的人前往報名申請加入一心會,他們似乎都在心底里把袁樹當作了這一次輿論風波的勝利者,已經開始向勝利者靠攏了。 楊賜、張濟、勛奇等人發現局勢越變越差,他們不僅沒有試探出袁樹的知識邊界,反倒把他們自己遼闊的知識盲區暴露給袁樹了。 其他人是什么心態,楊賜不知道,但是楊賜知道的是,他自己已經有點繃不住、輸不起了。 繼續這樣下去,別說議和,他這個帝師的身份能不能維持下去都不一定了。 難道,他也要以帝師之尊親自下場和袁樹辯駁? 萬一輸了,那不就廢了? 教導天子讀書的天下名士居然連他們口中侍讀都不配做的一介小兒打敗了。 楊賜不能接受這種局面。 也絕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他只能派出他最有能力的一批弟子前往向袁樹發起挑戰。 其余眾人也紛紛派遣他們最后的希望前往挑戰袁樹。 于是,在建寧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時候,袁樹率領麾下十三大將與楊賜等人的四十六名最強弟子展開巔峰對決。 他們以春秋和尚書為主要戰場展開激戰,于太學正門口的大廣場上,在數萬人的圍觀之下一戰到底。 此番對決有不少朝廷官員、達官顯貴,乃至于內廷宦官都前來觀看。 雒陽城里的各方勢力都十分關注這場分量極重的對決。 不少人心里都清楚,要是這些代表官學勢力高端戰斗力的精英們被袁樹擊敗了,官學勢力要想挽回局勢,就必須要出動真正的大佬們與袁樹正面對決。 否則,他們以后還怎么在太學里廝混? 袁樹當然沒有一開始就親自下場,而是先讓自己的十三大將們與之對戰,雙方激戰一個時辰,袁樹折損八名大將,而對方已經折損三十九人。 最后剩下的程立、魏甲和蘇初三人繼續對抗對方剩下的七人,又是一輪大戰,兩炷香時間過后,袁樹這邊只剩下魏甲一人,對方還剩三人。 于是魏甲一挑三,在袁樹的注視下爆發全部的能量,將對面三人一頓炮轟,戰至最后,還是倒下了。 最終以毫厘之差擊敗了魏甲的人,是楊賜的得意弟子、徐州東海人王朗。 于是王朗也成為了這一次巔峰對決中唯一一個能和袁樹面對面抗衡的人。 袁樹對他也很感興趣。 不知道為什么,得知面前這人是徐州人王朗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很想對他喊一句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看看他會不會大怒之下當場去世。 他覺得要是有這種可能的話,倒也不必麻煩諸葛亮了。不過王朗倒也不是這種人就是了,諸葛亮不曾罵過他,他也沒有被氣死,相反,他被認為是寬厚的長者。 他是什么人,袁樹不是很感興趣。 讓他感興趣的是,王朗面見他之后,似乎并沒有想要辯駁的想法,而是向他提了一個問題。 “袁君,我想知道,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真的可以拯救時局嗎?真的人人皆可成圣賢嗎?您為何如此肯定?如果做不到,又該如何?” 袁樹有些驚訝。 “好不容易走到這里,不與我辯經,卻要向我提問?” 王朗點了點頭。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您的對手,一定要辯經的話,一定會輸,這是毋庸置疑的,與其做一定沒有意義的事情,不如用這個時間向您請教心中困惑,我不知道如何解答,希望得到您的指點。” 望著面前年輕的“王司徒”那誠懇的眼神,袁樹想了想,緩緩點了點頭。 “你有困惑,那我就為你解答好了。” 袁樹邀請王朗坐下,整頓了一下衣冠。 “挽救時局,我相信是可以的,我不認為做不到,因為如果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我該如何說服眾人與我一起前行呢?” 王朗連忙追問。 “那如果辦不到呢?” “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袁樹笑著搖了搖頭:“關鍵不是能不能成功,因為能不能成功,并非是人力可以預測的,孔子推行儒學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學說能在數百年之后大行其道嗎?他不知道。 他活著的時候周游列國,前往各國推廣自己的學說,卻沒有幾個國家愿意接納他,沒有幾個國家愿意接受他的理念,他屢屢碰壁,直到最后也沒有見到自己克己復禮的理想成功實現。 但是他退縮了嗎?他或許會失望,卻從未退縮,一直都在堅持,不論是否有人愿意相信,有人愿意實踐,他從未退縮過,始終如一,這是他能夠成為當下吾輩眼中圣賢的重要緣由。 圣賢,并不一定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圣賢不會在沒有實現自己的主張的時候就去懷疑這條路是否可行,哪怕是一條死路,圣賢也會走到頭,看到盡頭之后,再作出改變。 所以我認為,我不會改變也不會懷疑我的學說,如果有人認為我是對的,要追隨我,那我歡迎,有人覺得我是錯的,不追隨我,我也接受,但是,我決不允許有人在我沒有付諸實踐之前就斷言我必然失敗。 沒有實踐過的事情,如何能算是失敗?沒有實踐過的學說,怎么就是歪理邪說、旁門左道?沒人知道,之所以有人說,是因為他們心術不正,他們的心臟了,所以看到什么都覺得是臟的。 而對于一個求學之人來說,保持心的純凈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信念的堅定是必需的,沒有這兩點,結果就和那些奸佞小人一樣,為世人所不齒,所以我的學說才是心學。” 王朗聽后,默默思考,緩緩點頭,似有所悟。 少頃,他又抬起頭看著袁樹。 “所以,您反對今文經學而提出自己的學說,是覺得今文經學已經失敗了?” “對,失敗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失敗了。” 袁樹搖頭道:“現在活著的,不過是借尸還魂的神鬼之說罷了,只顧抬頭望天,不去低頭看地,這種飄在空中的學說,如何能讓腳踏實地的人獲得幸福的生活呢?” “可當下的大漢國勢,真的如同您所說的那樣,已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王朗疑惑道:“如果已然如此,當下的情況應該更加兇險才是,應該早就混亂不堪了才是。”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袁樹嘆息道:“昔日文王已經得到三分之二的諸侯的聯合,卻依然對紂王稱臣,認為時機不對,不能伐紂,一直等到武王即位,才終于伐紂成功,這不是因為文王畏懼紂王,而是因為萬事萬物的演變需要時間。 莊稼不能一天長成,一個國家,無論多么的腐朽墮落,也不會在一瞬間就崩潰,當它出現崩潰的前兆的時候,往往還會堅持很長時間才會走上真正的末路,在此期間,并不會使得所有人都認為它將要崩塌。” 王朗一愣。 “您……認為大漢江山將要崩塌嗎?” “如果沒有人可以挽救大漢,那么大漢的崩塌并不是不可能的。” 袁樹嘆息道:“王君,大漢外有鮮卑、匈奴,內有災荒、流民,官員貪腐不知凡幾,執掌權柄者皆短視,只為自己,不為國家,地方豪強兼并土地,掠奪平民,造孽無數,此情此景,王君不覺得熟悉嗎?” (本章完) 我不是袁術 一百一十一 今文經學已經失敗了
休閑文學吧提供免費小說,請讀者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