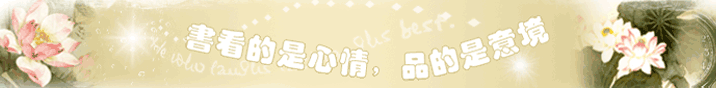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一個星際文明發展的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更新時間:2025-02-07 作者:少一尾的九尾貓
大國院士 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一個星際文明發展的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當徐川接到斯塔凡諾馬克秘書長的祝賀來電時,另一邊,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新聞發布會也正在同步進行。 相對比較往年物理學獎與化學獎會在不同的日期公布來說,今年這兩項自然科學獎選擇了在同一天公布。 原因很簡單,兩項諾獎的獲獎者,都是同一個人。 考慮到這個因素,物化兩院的評選委員會在互相商議了一下后決定將公布時間放到一起。 反正他們已經打破了常規,也不怕再震撼一點。 當然,除了這點外,他們也希望物化雙獎的榮譽 也正是因為如此,當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公布的時候,全世界都沸騰了起來。 在公布諾獎的新聞發布會結束后,國內外的媒體紛紛在第一時間轉發了相關的消息。 短短一個小時不到,徐川榮獲20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與諾貝爾化學獎的新聞消息便直接沖上了各大互聯網平臺的熱搜了。 臥槽?川神又雙叒叕獲獎了? 媽耶!物理獎和化學獎居然同時頒發給了一個人?這應該是歷史上的首次有人拿到不同類型的諾獎吧? 首次倒不是,上個世紀的居里夫人就分別拿到過物理獎和化學獎,只不過不是在同一年。除此之外還有獲得了化學獎與和平獎的萊納斯·鮑林,不過和平獎你懂的,狗都不要。 同一年拿到物理學獎和化學獎,諾獎可以這樣子頒發嗎?好奇。 理論上來說應該不行吧,但是規定這東西,本身就是用來打破的,川神拿兩枚諾獎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感覺沒有人比他更配! 如果算上18年的物理獎,川神他老人家已經拿到三枚了!而且這次頒獎的理由是強電統一理論的貢獻,但他還有暗物質粒子、室溫超導材料這兩項百分百能拿到諾獎的成果(如果發的話),這都批發諾獎勛章了,好家伙。 就沒人關心威騰教授嗎?!他終于拿到諾獎圓夢諾菲雙獎了!!!! 斜眼笑,學生帶著導師拿諾獎,這什么科幻中的故事?笑死了。 還有德利涅教授,一個數學家拿到了諾獎,這樣算下來,諾菲雙獎得主一下就有三位了。 不得不說,瑞典皇家科學院在同一年將物理學獎與化學獎頒發給同一個人的消息就如同冷水倒進熱油鍋一樣,在全世界都掀起了劇烈的討論。 畢竟,這個世界上能夠獲得兩枚諾貝爾獎的學者都屈指可數。 縱觀諾獎自1895年成立以來到現在一百多年,也就只有五個人而已。 更別提在同一年獲得了。 能夠在兩個不同領域分別獲得一枚諾貝爾獎,這意味著獲獎者至少要在兩個龐大的科學領域中做出全世界最頂尖的科研成果。 這個難度,拋開萊納斯·鮑林的化學獎與和平獎來說,全人類也只有居里夫人做到過。 而且她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拿到的,難度遠比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小。 畢竟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科技與學術的進步以及各個學科知識量的增加,幾乎是常人所無法想象的。 就拿物理來說,純物理學就有經典力學、熱力學和統計力學、電磁學、相對論、量子力學五大學科。 而多學科物理學還有化學物理學、地球物理學、經濟物理學、大氣物理學、生物物理學、醫學物理學、天文物理學七大學科。 兩大分類加起來總計12門學科,而這十二門物理學科下,幾乎每一個都有可以像樹枝一樣繼續細分下去的子學科。 如果真要統計的話,當代物理學的細枝領域已經超過了三位數,正在朝四位數前進。 而對于絕大部分的學者來說,能在這三位數的某一個細枝領域中做到極致,獲得其他物理學家的認可,就已經是需要用十幾年甚至是一輩子去完成的工作了。 甚至對于大部分的學者來說,他們根本就走不到某一個細枝領域的最前沿,并且有能力將這個前沿區域往前拓展那么一丁點。 所以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要想在不同大學科領域下同時拿到諾獎,難度真的太大太大了。 與此同時,另一邊。 下蜀航天基地,帶著任務前來航天局局長鄔遠康在向徐川了解清楚情況后已經離開。 辦公室中,帶著火星枯石菌最新研究實驗數據過來的華科院陳文澤教授輕輕的敲了敲敞開的門,走了進來。 “徐院士,常院士。” 打了個招呼后,他看向徐川,眼神中帶著濃濃的羨慕,笑著祝賀道:“恭喜徐院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 作為一名學者,諾貝爾獎可以說是他畢生的追求目標了。 當然,準確的來說,應該是畢生的夢想。 因為他從未將諾貝爾獎當做過自己的目標過。 畢竟夢想可以想,但目標是要追求和去努力實現的。 雖然說有時候他也會幻想一下自己能在五十歲之前被推薦一下評選科學院的院士,但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能獲得諾獎過。 因為以他的學術成就,距離諾獎實在是太遙遠了。 作為當前學術界公認的最高獎項,拿到了這枚獎章就意味著獲獎者可以在全世界都橫行無忌,再也無需為科研經費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煩惱。 然而就是這樣一份他想都不敢想的獎章,眼前這位比他要年輕近十歲的學者卻已經拿到了三枚! 三枚!整整三枚,刷新了學術界歷史,創造新史碑的數量啊! 這如何能不讓人羨慕? 沙發上,徐川笑著道:“謝謝,我也確實有些意外,沒想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委會這么破格,會同時給我頒發兩枚獎章。” 聞言,陳文澤教授有些好奇的開口道:“話說兩枚諾獎的話,應該可以攜帶28名家屬好友一起參加諾獎的晚宴吧。” 徐川看了他一眼,笑著道:“你想去?” 聽到這話,陳文澤摸了摸腦袋,嘿嘿笑道:“這可是諾獎晚宴,估計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沒參加過,肯定想去了!” 略微停頓了一下,他笑著道:“如果有多余的話,我可不可以申請一個名額啊。” “當然,如果不夠的話也沒關系,到時候徐院士幫忙拍兩張照片,讓我也遠程體驗一下。” 聽到這話,徐川笑了笑,道:“那就送你一個名額好了,兩枚諾獎附帶的28個名額我應該也用不了那么多。” 事實上,別說28個參加諾獎晚宴的名額了,就是14個對他來說都足夠用了。 畢竟他的朋友雖多,但好友一直就那么幾個。 這段時間為了找到治療火星枯石菌感染的辦法,眼前這位也的確幫了他不少的忙,代替他在主持國際火星生命研究項目,就當是給他的獎勵好了。 聽到徐川的話,陳文澤眼前一亮,快速的說道:“謝謝徐院士!” 閑聊了幾句有關于諾貝爾獎的事情后,陳文澤將手中攜帶過來的實驗報告一人一份遞給了徐川和常華祥,開口說起了正事。 “關于火星枯石菌的研究,目前月華臺科研基地遭受感染的人員都已經注射了免疫蛋白藥物。除去此前受感染最嚴重的四名航天員外,其他人的身體指標都已經恢復到了正常人的范疇。” “至于劉楊和江新林的身體硅基異化結構,還需要等待后續的觀察,以確認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恢復正常的人體結構。” “另外.” 停頓了一下,他看向徐川,接著道:“關于火星枯石菌感染動物的研究,通過感染后的小白鼠身體組織切片,以及活體實驗觀察,我們已經初步確認了這種細菌的感染模式。” “如果是從感染模式以及與宿主的存在關系來說,這是一種地球上尚未出現過的形式,既非細菌,也非病毒。” 聞言,徐川有些好奇的看了過去:“但我沒記錯的話,從之前的實驗數據來看,它與宿主的關系是寄生關系吧?” “這種火星生命在進入人體細胞后,完全依賴宿主細胞才能生存和繁殖。” 陳文澤教授點了點頭,解釋道:“是的,如果是單純的從這方面來看,火星枯石菌屬于病毒類型。” “但生物學界判斷一種生物的種類往往需要從多方面條件來進行。” “雖然說病毒對宿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存在著‘協同演化’的關系,但從宿主的角度來觀察,這種協同演化是被動型的。” “因為不進化出免疫或殺死對應病毒的手段,宿主細胞就會死亡。” “而火星枯石菌則不同,它的確需要宿主細胞來提供營養物質進行繁衍生存。但在寄生的過程中它就像是穿上了一件隱身衣一樣,很難直接觸發宿主的免疫系統。” “而在寄生的過程中,它還會借助宿主細胞的營養物質合成一種激素。” “這種枯石激素通過寄生細胞釋放出來后會進入宿主的體液循環,進而參與宿主的代謝活動。” “并且這種激素還能夠進入類骨組織結構中,與宿主體內游離的偏硅酸進行結構,產生全新的硅基蛋白。” “這也是感染了火星枯石菌的人身體結構組織會出現硅基化變異的原因。它與我們之前推測的原生細胞被改造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與地球上的病毒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 “而如果要對其劃分一種生命形式的話,從目前的觀察到的情況來進行歸類的話,應該對其建立一個全新的分類。” 說到這,陳文澤教授看向徐川,眼神中又帶上了濃濃的羨慕。 雖然說劃分一種生物的種類理論上來說應該是生物學界內部的事情,但如果說最有資格對這種火星枯石菌進行種類劃分的,毫無疑問是眼前這位了。 畢竟火星枯石菌是在他主導的載人登火工程中發現的,而治療這種火星細菌感染的方法也是他找到的。 “共生、枯石激素、代謝異化,有點意思。” 聽著陳文澤教授的解釋,徐川摸了摸下巴,眼神中帶著饒有興趣的神色。 思索了一會后,他看向陳文澤教授,開口問道:“能找到是哪一段基因結構在控制這種激素的合成嗎?” 陳文澤點了點頭,道:“應該沒問題,只不過需要一些時間。” 微微頓了頓,他接著道:“枯石菌的遺傳基因結構突破已經全部做出來了,后續我們會針對性的進行每一段完整的遺傳片段進行基因編輯實驗,以了解不同的片段會帶來什么不同的功能。” 火星枯石菌的遺傳基因的確比常規的病毒細菌要復雜不少,但相對比對人類的每一種基因片段進行編輯實驗了解它們的功能來說,就要簡單太多了。 尤其是能夠制造蛋白質的編碼序列,數量相對比非編碼序列來說通常僅占比不到百分之五而已。 就像人類的基因數量比原先預期的少得多,其中的外顯子,也就是能夠制造蛋白質的編碼序列,只占總長度的約1.5。 而這種火星枯石菌的外顯子,即編碼序列很顯然比人類更少,破譯它們需要的時間也更少。 徐川點了點頭,道:“那交給你們一個任務。” “簡單的來說,就是找到這種控制硅基蛋白合成激素的基因片段,對其進行及分析,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再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嘗試性的去使用碳基、鈣基或硫基等結構去取代原本的片段。” 聽到這話,陳文澤教授眼眸一動,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深吸了口氣看了過來,忍不住問道:“您這是” 徐川笑了笑,道:“如果能夠解決掉火星枯石菌改造異化人體結構的副作用,那么對于人類來說這就是一次全新的進化方向。”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道:“對于已經開始進行太空探索的人類來說,面對宇宙中各種復雜環境的行星將是未來最常見的事情。” “相對比整個大宇宙來說,人類身體的適應環境的確太過于單一脆弱。只能生存在固定類型的星球上。” “而現在我們面前就有另外一條路。” “如果說人類文明真想要走出地球,那么除了尋找適宜生存的外星球,以及改造條件相近的外星球讓其變得宜居以外,讓人類主動進化適應不同的外星環境,或許也是一條路。” “或許在當前看來它可能極大的違背了倫理與道德,也會引起極大的爭議。” “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先進行技術儲備。” 大國院士 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一個星際文明發展的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當徐川接到斯塔凡諾馬克秘書長的祝賀來電時,另一邊,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新聞發布會也正在同步進行。 相對比較往年物理學獎與化學獎會在不同的日期公布來說,今年這兩項自然科學獎選擇了在同一天公布。 原因很簡單,兩項諾獎的獲獎者,都是同一個人。 考慮到這個因素,物化兩院的評選委員會在互相商議了一下后決定將公布時間放到一起。 反正他們已經打破了常規,也不怕再震撼一點。 當然,除了這點外,他們也希望物化雙獎的榮譽 也正是因為如此,當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公布的時候,全世界都沸騰了起來。 在公布諾獎的新聞發布會結束后,國內外的媒體紛紛在第一時間轉發了相關的消息。 短短一個小時不到,徐川榮獲20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與諾貝爾化學獎的新聞消息便直接沖上了各大互聯網平臺的熱搜了。 臥槽?川神又雙叒叕獲獎了? 媽耶!物理獎和化學獎居然同時頒發給了一個人?這應該是歷史上的首次有人拿到不同類型的諾獎吧? 首次倒不是,上個世紀的居里夫人就分別拿到過物理獎和化學獎,只不過不是在同一年。除此之外還有獲得了化學獎與和平獎的萊納斯·鮑林,不過和平獎你懂的,狗都不要。 同一年拿到物理學獎和化學獎,諾獎可以這樣子頒發嗎?好奇。 理論上來說應該不行吧,但是規定這東西,本身就是用來打破的,川神拿兩枚諾獎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感覺沒有人比他更配! 如果算上18年的物理獎,川神他老人家已經拿到三枚了!而且這次頒獎的理由是強電統一理論的貢獻,但他還有暗物質粒子、室溫超導材料這兩項百分百能拿到諾獎的成果(如果發的話),這都批發諾獎勛章了,好家伙。 就沒人關心威騰教授嗎?!他終于拿到諾獎圓夢諾菲雙獎了!!!! 斜眼笑,學生帶著導師拿諾獎,這什么科幻中的故事?笑死了。 還有德利涅教授,一個數學家拿到了諾獎,這樣算下來,諾菲雙獎得主一下就有三位了。 不得不說,瑞典皇家科學院在同一年將物理學獎與化學獎頒發給同一個人的消息就如同冷水倒進熱油鍋一樣,在全世界都掀起了劇烈的討論。 畢竟,這個世界上能夠獲得兩枚諾貝爾獎的學者都屈指可數。 縱觀諾獎自1895年成立以來到現在一百多年,也就只有五個人而已。 更別提在同一年獲得了。 能夠在兩個不同領域分別獲得一枚諾貝爾獎,這意味著獲獎者至少要在兩個龐大的科學領域中做出全世界最頂尖的科研成果。 這個難度,拋開萊納斯·鮑林的化學獎與和平獎來說,全人類也只有居里夫人做到過。 而且她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拿到的,難度遠比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小。 畢竟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科技與學術的進步以及各個學科知識量的增加,幾乎是常人所無法想象的。 就拿物理來說,純物理學就有經典力學、熱力學和統計力學、電磁學、相對論、量子力學五大學科。 而多學科物理學還有化學物理學、地球物理學、經濟物理學、大氣物理學、生物物理學、醫學物理學、天文物理學七大學科。 兩大分類加起來總計12門學科,而這十二門物理學科下,幾乎每一個都有可以像樹枝一樣繼續細分下去的子學科。 如果真要統計的話,當代物理學的細枝領域已經超過了三位數,正在朝四位數前進。 而對于絕大部分的學者來說,能在這三位數的某一個細枝領域中做到極致,獲得其他物理學家的認可,就已經是需要用十幾年甚至是一輩子去完成的工作了。 甚至對于大部分的學者來說,他們根本就走不到某一個細枝領域的最前沿,并且有能力將這個前沿區域往前拓展那么一丁點。 所以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要想在不同大學科領域下同時拿到諾獎,難度真的太大太大了。 與此同時,另一邊。 下蜀航天基地,帶著任務前來航天局局長鄔遠康在向徐川了解清楚情況后已經離開。 辦公室中,帶著火星枯石菌最新研究實驗數據過來的華科院陳文澤教授輕輕的敲了敲敞開的門,走了進來。 “徐院士,常院士。” 打了個招呼后,他看向徐川,眼神中帶著濃濃的羨慕,笑著祝賀道:“恭喜徐院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 作為一名學者,諾貝爾獎可以說是他畢生的追求目標了。 當然,準確的來說,應該是畢生的夢想。 因為他從未將諾貝爾獎當做過自己的目標過。 畢竟夢想可以想,但目標是要追求和去努力實現的。 雖然說有時候他也會幻想一下自己能在五十歲之前被推薦一下評選科學院的院士,但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能獲得諾獎過。 因為以他的學術成就,距離諾獎實在是太遙遠了。 作為當前學術界公認的最高獎項,拿到了這枚獎章就意味著獲獎者可以在全世界都橫行無忌,再也無需為科研經費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煩惱。 然而就是這樣一份他想都不敢想的獎章,眼前這位比他要年輕近十歲的學者卻已經拿到了三枚! 三枚!整整三枚,刷新了學術界歷史,創造新史碑的數量啊! 這如何能不讓人羨慕? 沙發上,徐川笑著道:“謝謝,我也確實有些意外,沒想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委會這么破格,會同時給我頒發兩枚獎章。” 聞言,陳文澤教授有些好奇的開口道:“話說兩枚諾獎的話,應該可以攜帶28名家屬好友一起參加諾獎的晚宴吧。” 徐川看了他一眼,笑著道:“你想去?” 聽到這話,陳文澤摸了摸腦袋,嘿嘿笑道:“這可是諾獎晚宴,估計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沒參加過,肯定想去了!” 略微停頓了一下,他笑著道:“如果有多余的話,我可不可以申請一個名額啊。” “當然,如果不夠的話也沒關系,到時候徐院士幫忙拍兩張照片,讓我也遠程體驗一下。” 聽到這話,徐川笑了笑,道:“那就送你一個名額好了,兩枚諾獎附帶的28個名額我應該也用不了那么多。” 事實上,別說28個參加諾獎晚宴的名額了,就是14個對他來說都足夠用了。 畢竟他的朋友雖多,但好友一直就那么幾個。 這段時間為了找到治療火星枯石菌感染的辦法,眼前這位也的確幫了他不少的忙,代替他在主持國際火星生命研究項目,就當是給他的獎勵好了。 聽到徐川的話,陳文澤眼前一亮,快速的說道:“謝謝徐院士!” 閑聊了幾句有關于諾貝爾獎的事情后,陳文澤將手中攜帶過來的實驗報告一人一份遞給了徐川和常華祥,開口說起了正事。 “關于火星枯石菌的研究,目前月華臺科研基地遭受感染的人員都已經注射了免疫蛋白藥物。除去此前受感染最嚴重的四名航天員外,其他人的身體指標都已經恢復到了正常人的范疇。” “至于劉楊和江新林的身體硅基異化結構,還需要等待后續的觀察,以確認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恢復正常的人體結構。” “另外.” 停頓了一下,他看向徐川,接著道:“關于火星枯石菌感染動物的研究,通過感染后的小白鼠身體組織切片,以及活體實驗觀察,我們已經初步確認了這種細菌的感染模式。” “如果是從感染模式以及與宿主的存在關系來說,這是一種地球上尚未出現過的形式,既非細菌,也非病毒。” 聞言,徐川有些好奇的看了過去:“但我沒記錯的話,從之前的實驗數據來看,它與宿主的關系是寄生關系吧?” “這種火星生命在進入人體細胞后,完全依賴宿主細胞才能生存和繁殖。” 陳文澤教授點了點頭,解釋道:“是的,如果是單純的從這方面來看,火星枯石菌屬于病毒類型。” “但生物學界判斷一種生物的種類往往需要從多方面條件來進行。” “雖然說病毒對宿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存在著‘協同演化’的關系,但從宿主的角度來觀察,這種協同演化是被動型的。” “因為不進化出免疫或殺死對應病毒的手段,宿主細胞就會死亡。” “而火星枯石菌則不同,它的確需要宿主細胞來提供營養物質進行繁衍生存。但在寄生的過程中它就像是穿上了一件隱身衣一樣,很難直接觸發宿主的免疫系統。” “而在寄生的過程中,它還會借助宿主細胞的營養物質合成一種激素。” “這種枯石激素通過寄生細胞釋放出來后會進入宿主的體液循環,進而參與宿主的代謝活動。” “并且這種激素還能夠進入類骨組織結構中,與宿主體內游離的偏硅酸進行結構,產生全新的硅基蛋白。” “這也是感染了火星枯石菌的人身體結構組織會出現硅基化變異的原因。它與我們之前推測的原生細胞被改造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與地球上的病毒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 “而如果要對其劃分一種生命形式的話,從目前的觀察到的情況來進行歸類的話,應該對其建立一個全新的分類。” 說到這,陳文澤教授看向徐川,眼神中又帶上了濃濃的羨慕。 雖然說劃分一種生物的種類理論上來說應該是生物學界內部的事情,但如果說最有資格對這種火星枯石菌進行種類劃分的,毫無疑問是眼前這位了。 畢竟火星枯石菌是在他主導的載人登火工程中發現的,而治療這種火星細菌感染的方法也是他找到的。 “共生、枯石激素、代謝異化,有點意思。” 聽著陳文澤教授的解釋,徐川摸了摸下巴,眼神中帶著饒有興趣的神色。 思索了一會后,他看向陳文澤教授,開口問道:“能找到是哪一段基因結構在控制這種激素的合成嗎?” 陳文澤點了點頭,道:“應該沒問題,只不過需要一些時間。” 微微頓了頓,他接著道:“枯石菌的遺傳基因結構突破已經全部做出來了,后續我們會針對性的進行每一段完整的遺傳片段進行基因編輯實驗,以了解不同的片段會帶來什么不同的功能。” 火星枯石菌的遺傳基因的確比常規的病毒細菌要復雜不少,但相對比對人類的每一種基因片段進行編輯實驗了解它們的功能來說,就要簡單太多了。 尤其是能夠制造蛋白質的編碼序列,數量相對比非編碼序列來說通常僅占比不到百分之五而已。 就像人類的基因數量比原先預期的少得多,其中的外顯子,也就是能夠制造蛋白質的編碼序列,只占總長度的約1.5。 而這種火星枯石菌的外顯子,即編碼序列很顯然比人類更少,破譯它們需要的時間也更少。 徐川點了點頭,道:“那交給你們一個任務。” “簡單的來說,就是找到這種控制硅基蛋白合成激素的基因片段,對其進行及分析,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再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嘗試性的去使用碳基、鈣基或硫基等結構去取代原本的片段。” 聽到這話,陳文澤教授眼眸一動,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深吸了口氣看了過來,忍不住問道:“您這是” 徐川笑了笑,道:“如果能夠解決掉火星枯石菌改造異化人體結構的副作用,那么對于人類來說這就是一次全新的進化方向。”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道:“對于已經開始進行太空探索的人類來說,面對宇宙中各種復雜環境的行星將是未來最常見的事情。” “相對比整個大宇宙來說,人類身體的適應環境的確太過于單一脆弱。只能生存在固定類型的星球上。” “而現在我們面前就有另外一條路。” “如果說人類文明真想要走出地球,那么除了尋找適宜生存的外星球,以及改造條件相近的外星球讓其變得宜居以外,讓人類主動進化適應不同的外星環境,或許也是一條路。” “或許在當前看來它可能極大的違背了倫理與道德,也會引起極大的爭議。” “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先進行技術儲備。” 大國院士 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一個星際文明發展的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休閑文學吧提供免費小說,請讀者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