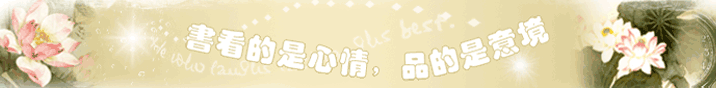第八百六十五章 遼使入京
更新時間:2025-02-05 作者:要離刺荊軻
我在現代留過學 第八百六十五章 遼使入京
元祐二年七月乙未(初十)。 開封府、滑縣、白馬渡。 載著遼國使團的船只,緩緩靠岸。 隨著船舶靠岸,兩個持著節旄的遼國貴族,率著數十名遼國官吏,在大宋官軍的保(監)護(視)下,走下舷梯。 頓時,鼓樂響起。 蕭德崇聽著樂聲,笑了起來。 “此詩之《鹿鳴》吧?”他微笑著問著自己身邊的副使張琳。 張琳點頭:“回節度,正是《鹿鳴》之樂!” 蕭德崇的嘴角,頓時就彎了起來。 他想起了去年,宋使胡宗愈,來到大遼,朝賀大遼天子生辰時。 他被任命為館伴使,迎接宋使入境。 當時,蕭德崇奉旨,在宋使入境時,命樂隊演奏詩經的《堂棣》。 棠棣之義,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 其意思就是隱晦的告訴宋庭——咱們是兄弟之邦啊,高麗那是外人,你們要幫我們啊! 然而,當時的那個宋使胡宗愈,在聽到棠棣之樂后,一臉的不高興。 在和他禮節性的寒暄時,更是陰陽怪氣的說了一堆諸如‘啊呀,北朝居然也知道《詩經》?’一類的話。 搞得好像,大遼在其眼中,就和阻卜人、女直人一般,屬于不通禮法的蠻夷。 當時可把蕭德崇氣炸了! 可宋使向來如此,他們在出使遼境時,總是會想方設法的和遼人在關乎正統、地位的細節上爭執,且從不退讓。 也就是如今的遼國,精力都在高麗方向。 同時遼國也有求于宋庭,為了兩國兄弟之邦的盟好大局,蕭德崇當時是捏著鼻子忍了的。 但,彼時他也發誓,早晚有一日要找回場子。 至少,要叫那個宋使胡宗愈,在他面前低頭。 不過,現在,當他來到宋境,聽到這南朝用著《詩經》之樂來歡迎他的時候。 蕭德崇內心的不滿,頓時煙消云散。 盡管《鹿鳴》之樂,只是歡迎遠方客人而已。 可,這是詩經啊! 是諸夏內部外交的時候,才會用到的禮樂。 這意味著什么? 南朝終于正視大遼了! 一種滿足感和成就感,在蕭德崇心中油然而生。 讓他心情愉悅,滿心歡喜。 白馬渡不遠,就是白馬鎮。 這是一個依托航運而興起的市鎮。 算是府界內比較大的商業貿易市鎮了。 過去就常年有著數百名坐商,在此經營買賣。 自宋遼交子貿易興起后,在此謀生的商賈就更多了。 如今,可能已經有上千名商賈在此營生。 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以及雇工、相關官吏、駐軍加起來,已超過兩萬! 這直接使得白馬鎮的規模,在短短一年內,就擴大了一倍! 此刻,白馬鎮的商賈們,都已從鎮中蜂擁而出,伸長了脖子,看向遠方的渡口。 盡管官兵們,拉起了厚厚的封鎖線,將人們攔在官道外。 可這依然擋不住,大宋的‘良善商賈們’的拳拳忠君愛國之心! 是的! 隨著汴京新報和汴京義報,在過去半個月的狂轟濫炸。 如今,這開封府的大宋商賈們,就連走路,都比過去硬氣了。 一個個開口就是:吾乃義商(仁商)! 為什么呢? 因為我雇了人啊! 按照汴京義報上的文章所暗示的內容,義商們的仁義含量,應該直接和其雇傭的雇工數量成正比! 雇的人越多,此人就越‘仁義’。 于是,在汴京城里開了上百家孫家燒朱鋪的大宋皇商孫賜,成為了汴京呼保義,開封及時雨。 因為,孫賜的各項產業加起來,雇工數量超過了一萬(當然,是加上了依附孫家正店的腳鋪的雇工,但實際上,腳鋪是分銷商,并不受孫賜雇傭,也不拿孫賜的工錢)。 于是,孫賜直接在自家正店門口,掛起了兩面酒旗。 左邊的酒旗,寫著一個大大的仁字,右邊的酒旗,寫著一個個大大的義字。 明晃晃的打出了仁義行商的旗幟。 本來,這種高調的豪商,必然引來官府鐵拳、覬覦乃至于撕咬、分食。 然而…… 開封府和街道司還有店宅務,就像瞎了一樣,根本看不見。 據說,已經被罷免待罪在家的前權知開封府蔡京蔡元長,還邀請了孫賜參加他家的家宴,席間多有贊賞云云。 于是,京城中的商賈,瞬間懂了。 雇工數量比較多的,就學著孫賜,掛起‘仁義’的招牌。 雇工數量比較少的,就掛個仁字或者義字。 一時間,汴京商賈皆仁義,個個都是儒商。 開口閉口,都開始動不動就子曰,之乎者也了。 好些道學先生,見了都是腦瓜子疼。 但,坊間輿論也好,士大夫公議也罷。 都無視了這些老學究的雜音。 他們辛辛苦苦寫的文章,投稿去汴京義報,直接石沉大海。 搞不好第二天,汴京義報直接刊載一篇‘奉勸’他們要認真讀書,讀好書,認真領會圣人微言大義的文章,不要聽風就是雨,更不要大驚小怪。 一個個臉打的啪啪響。 而白馬鎮距離汴京,不過百里。 昨天發行的汴京新報、汴京義報,今天就能送到白馬鎮來。 所以,白馬鎮的商賈們,自然也緊跟著汴京城里的商賈,一個個都開始高調起來。 此刻,他們就烏泱泱的擠在官道兩側,翹首望向正在下船的遼國使團。 “北使此來,恐怕還是來和官家談交子的……”好多人都議論著。 “那不?” “聽說北朝此番,又運來了數十萬兩白銀,請求官家給他們再印個幾百萬貫交子呢!” “真的嗎?” “真的不能再真了!” “我弟弟的渾家的小舅子在開封府當差,他親口告訴我的……” “哎呀呀,又有錢賺了!” “不對!” “是應該又可以增長仁義了!” 生意擴大了,自然要雇人,雇人越多,仁義越多。 頓時,許多人都覺得,自己體內的仁義之魂,已經在燃燒了。 這朝廷里的大人物們也真是的! 早說多雇工,就能變成仁人義士。 那俺們,肯定會大力擴張自己的買賣,拼命雇工啊! 在商賈們嘰嘰喳喳的議論中,刑恕騎著馬,在一隊禁軍的簇擁下,來到了這白馬鎮外的官道上,準備著歡迎遼使。 在他身邊,有一輛馬車,車上坐著耶律琚和耶律永昌。 “和叔……那位就是蕭德崇了……”耶律琚掀開車簾,看著出現在道路上,被宋軍簇擁著的遼國使團,指著在人群最前方的那位高大的遼國權貴說道:“其乃四國舅房的嫡脈所出,為人素來高傲……” 刑恕點點頭,作為大宋負責對外關系的大臣。 刑恕對遼國政治及其淵源,自然是用過功的。 何況,他還能從耶律琚和耶律永昌等人處了解、詢問。 故此他知道,不要看遼國后族,皆漢姓蕭氏,就以為他們系出同源。 但只要仔細研究,就會知道,漢姓蕭氏之外,遼國后族還有契丹姓氏。 而這些‘蕭姓’外戚的契丹姓氏,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一般來說,國舅家主要出自五個不同氏族,這就是遼人口中所謂的國舅五房了。 更正統的稱呼應該是:二國舅帳五房。 二國舅帳者,審密氏二姓,既契丹立國以前,還是部落聯盟時代,就專門和部落首領聯姻的審密氏拔里、乙室已兩族。 然而…… 其實,現在真正的審密氏拔里、乙室已兩族的人,早就被人殺光了。 遼國早期,混亂的政治,讓帝系都轉移了好幾次。 作為外戚的國舅帳,更是殺的人頭滾滾。 所以,現在的所謂二國舅帳五房,早不知道換了多少次血了。 蕭德崇所在的所謂國舅四房,就是承天太后時代才出現的乙室已少翁房。 這一房,系出承天太后父族蕭思溫家族——乃是蕭思溫幼子這一脈。 與如今遼國的后族,蕭思坦(廢皇后蕭觀音)所在的拔里氏國舅兩房,完全不是一個源頭——他們都是述律家族的后人。 當然,真述律還是假述律,就沒有人知道了。 刑恕遠遠的看著,那個騎在馬上,穿著遼國貴族服飾的中年男子,眼睛慢慢瞇起來:“高傲嗎?” 傲就傲吧! 當初,耶律琚入朝的時候,不也挺高傲的嗎? “他可有什么喜歡的我朝人物?”刑恕扭頭問道。 耶律琚想了想,答道:“據在下所知,此人不太喜好詩詞,倒是從小就喜歡聽人說蘇秦張儀的故事……” “蘇秦張儀?”刑恕咧嘴一笑:“吾也喜歡啊!” 他本來就是縱橫派,在被官家任用,主管大宋對外的外交后,就更喜歡了。 “待吾與之親近親近!” 喜歡蘇秦張儀好啊。 因為蘇秦張儀,從不在乎,自己給誰效力? 他們只在乎,誰會重用自己,以給自己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舞臺。 那蕭德崇在遼國,得到了他的舞臺嗎? 刑恕知道,至少現在還沒有。 不然他就不會這么默默無聞。 不然,就該是他坐在耶律琚和耶律永昌的所在的地方。 “蕭德崇旁的,就是張琳……此乃沈州人,少有大志,紛紛讀書,終中進士,為我主所愛……”耶律永昌從馬車里探出頭來,給刑恕介紹道:“此人,素以清流自居,好詩詞文章,乃是我大遼有名的詞臣。” 刑恕聽著,笑得更歡樂了。 好詩詞文章? 那他就來對地方了! 說話間,遠方官道上的遼使隊伍已經越來越近。 耶律琚和耶律永昌也就放下了車簾。 刑恕則翻身下馬,微笑著迎上前去,對著遼人使團隊伍,微微拱手一禮:“奉大宋皇帝陛下旨意,大宋翰林學士充館伴使刑恕,特來迎接諸位北國使臣!” 蕭德崇自然早早的看到了,在官道上的刑恕——刑恕穿著大宋的紫袍公服,頭戴著展腳幞頭,目標無比顯目,想不注意都難! 于是,他見到刑恕拱手,自也停下腳步,高舉代表大遼天子的節旄,微微欠身行禮:“奉大遼天子旨意,大遼崇儀軍節度使蕭德崇……” 與其并列而行,只是稍稍落后一個身位,穿著緋袍的張琳,也拱手問禮:“大遼中散大夫、充干文閣待制、守太常少卿張琳……” “特來恭賀大宋太皇太后坤寧圣節,以敘兩國兄弟之盟好!” 刑恕聽著,立刻再拱手,然后挺直腰桿,面朝皇城方向,鄭重的拿出一封敕書,抑揚頓挫的念了起來。 “卿久勤軺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這是學士院寫好的,用來宣讀給遼國使臣的慰勞敕書。 屬于是澶淵之盟的約定——兩國定期互遣使臣,修好交往,彼此使臣入境,自然要各頒詔書慰勉。 宋使入遼如此,遼使入宋亦如此。 在過去,這個程序是在遼使入境大宋的時候宣讀,所以叫‘茶馬敕’。 一般都是賜下茶水,以供遼使飲用、解渴、去乏。 并供給遼人草料,以便遼國使團的牲畜能補充一下體力。 但從去年開始,按照宋遼兩國的新約定。 降敕賜物的地點,從邊境改到了京城(皇帝捺缽所在)。 這是為了增進兩國的兄弟之盟。 同時,也是為了表達,兩國君主對兩國關系的重視——一入境就降下敕書,看似友好,實則在使團入境的時候,就會有著大量兵馬順勢將之保護起來。 如今,到京城(皇帝捺缽所在)附近,再降下敕書,就意味著,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彼此使團都能有一段相對輕松、自由的活動時間。 雖然說,依然是要在地方官監視下,走規定的路線。 但起碼,能夠近距離的觀察途徑地區的風土人情、地理地貌、交通河流。 而不是像囚犯一樣,一路被大批兵馬,死死圍住,恨不得連光都給使團遮住。 這是大宋方面開始自信的表現——過去,遼人其實無所謂宋庭使團在其境內怎么觀察風土人情、考察地理地貌、交通河流。 不然,大宋方面,也不會有那么多出使遼國的大臣能在回國后,寫下各種有關遼國的筆記甚至繪制出地圖。 對使團嚴防死守的,一直是大宋這邊。 畢竟,恐遼癥晚期患者,在大宋從宮中到朝中,從來不缺。 被遼人稍微恐嚇一下,就兩股瑟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甚至都不需要遼人恐嚇,自己就先亂了陣腳——比方說,造成了無數災難,使得數十軍州的數百萬百姓,在洪水中哀嚎的兩次回河,之所以會被推動,就是因為大宋方面,渴望黃河回到故道,擋住薛定諤的可能會從幽燕長驅直入的遼國鐵騎。 為此,郎心如鐵,哪怕撞得頭破血流,也依舊有無數人在為這個計劃癡迷。 我在現代留過學 第八百六十五章 遼使入京
元祐二年七月乙未(初十)。 開封府、滑縣、白馬渡。 載著遼國使團的船只,緩緩靠岸。 隨著船舶靠岸,兩個持著節旄的遼國貴族,率著數十名遼國官吏,在大宋官軍的保(監)護(視)下,走下舷梯。 頓時,鼓樂響起。 蕭德崇聽著樂聲,笑了起來。 “此詩之《鹿鳴》吧?”他微笑著問著自己身邊的副使張琳。 張琳點頭:“回節度,正是《鹿鳴》之樂!” 蕭德崇的嘴角,頓時就彎了起來。 他想起了去年,宋使胡宗愈,來到大遼,朝賀大遼天子生辰時。 他被任命為館伴使,迎接宋使入境。 當時,蕭德崇奉旨,在宋使入境時,命樂隊演奏詩經的《堂棣》。 棠棣之義,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 其意思就是隱晦的告訴宋庭——咱們是兄弟之邦啊,高麗那是外人,你們要幫我們啊! 然而,當時的那個宋使胡宗愈,在聽到棠棣之樂后,一臉的不高興。 在和他禮節性的寒暄時,更是陰陽怪氣的說了一堆諸如‘啊呀,北朝居然也知道《詩經》?’一類的話。 搞得好像,大遼在其眼中,就和阻卜人、女直人一般,屬于不通禮法的蠻夷。 當時可把蕭德崇氣炸了! 可宋使向來如此,他們在出使遼境時,總是會想方設法的和遼人在關乎正統、地位的細節上爭執,且從不退讓。 也就是如今的遼國,精力都在高麗方向。 同時遼國也有求于宋庭,為了兩國兄弟之邦的盟好大局,蕭德崇當時是捏著鼻子忍了的。 但,彼時他也發誓,早晚有一日要找回場子。 至少,要叫那個宋使胡宗愈,在他面前低頭。 不過,現在,當他來到宋境,聽到這南朝用著《詩經》之樂來歡迎他的時候。 蕭德崇內心的不滿,頓時煙消云散。 盡管《鹿鳴》之樂,只是歡迎遠方客人而已。 可,這是詩經啊! 是諸夏內部外交的時候,才會用到的禮樂。 這意味著什么? 南朝終于正視大遼了! 一種滿足感和成就感,在蕭德崇心中油然而生。 讓他心情愉悅,滿心歡喜。 白馬渡不遠,就是白馬鎮。 這是一個依托航運而興起的市鎮。 算是府界內比較大的商業貿易市鎮了。 過去就常年有著數百名坐商,在此經營買賣。 自宋遼交子貿易興起后,在此謀生的商賈就更多了。 如今,可能已經有上千名商賈在此營生。 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以及雇工、相關官吏、駐軍加起來,已超過兩萬! 這直接使得白馬鎮的規模,在短短一年內,就擴大了一倍! 此刻,白馬鎮的商賈們,都已從鎮中蜂擁而出,伸長了脖子,看向遠方的渡口。 盡管官兵們,拉起了厚厚的封鎖線,將人們攔在官道外。 可這依然擋不住,大宋的‘良善商賈們’的拳拳忠君愛國之心! 是的! 隨著汴京新報和汴京義報,在過去半個月的狂轟濫炸。 如今,這開封府的大宋商賈們,就連走路,都比過去硬氣了。 一個個開口就是:吾乃義商(仁商)! 為什么呢? 因為我雇了人啊! 按照汴京義報上的文章所暗示的內容,義商們的仁義含量,應該直接和其雇傭的雇工數量成正比! 雇的人越多,此人就越‘仁義’。 于是,在汴京城里開了上百家孫家燒朱鋪的大宋皇商孫賜,成為了汴京呼保義,開封及時雨。 因為,孫賜的各項產業加起來,雇工數量超過了一萬(當然,是加上了依附孫家正店的腳鋪的雇工,但實際上,腳鋪是分銷商,并不受孫賜雇傭,也不拿孫賜的工錢)。 于是,孫賜直接在自家正店門口,掛起了兩面酒旗。 左邊的酒旗,寫著一個大大的仁字,右邊的酒旗,寫著一個個大大的義字。 明晃晃的打出了仁義行商的旗幟。 本來,這種高調的豪商,必然引來官府鐵拳、覬覦乃至于撕咬、分食。 然而…… 開封府和街道司還有店宅務,就像瞎了一樣,根本看不見。 據說,已經被罷免待罪在家的前權知開封府蔡京蔡元長,還邀請了孫賜參加他家的家宴,席間多有贊賞云云。 于是,京城中的商賈,瞬間懂了。 雇工數量比較多的,就學著孫賜,掛起‘仁義’的招牌。 雇工數量比較少的,就掛個仁字或者義字。 一時間,汴京商賈皆仁義,個個都是儒商。 開口閉口,都開始動不動就子曰,之乎者也了。 好些道學先生,見了都是腦瓜子疼。 但,坊間輿論也好,士大夫公議也罷。 都無視了這些老學究的雜音。 他們辛辛苦苦寫的文章,投稿去汴京義報,直接石沉大海。 搞不好第二天,汴京義報直接刊載一篇‘奉勸’他們要認真讀書,讀好書,認真領會圣人微言大義的文章,不要聽風就是雨,更不要大驚小怪。 一個個臉打的啪啪響。 而白馬鎮距離汴京,不過百里。 昨天發行的汴京新報、汴京義報,今天就能送到白馬鎮來。 所以,白馬鎮的商賈們,自然也緊跟著汴京城里的商賈,一個個都開始高調起來。 此刻,他們就烏泱泱的擠在官道兩側,翹首望向正在下船的遼國使團。 “北使此來,恐怕還是來和官家談交子的……”好多人都議論著。 “那不?” “聽說北朝此番,又運來了數十萬兩白銀,請求官家給他們再印個幾百萬貫交子呢!” “真的嗎?” “真的不能再真了!” “我弟弟的渾家的小舅子在開封府當差,他親口告訴我的……” “哎呀呀,又有錢賺了!” “不對!” “是應該又可以增長仁義了!” 生意擴大了,自然要雇人,雇人越多,仁義越多。 頓時,許多人都覺得,自己體內的仁義之魂,已經在燃燒了。 這朝廷里的大人物們也真是的! 早說多雇工,就能變成仁人義士。 那俺們,肯定會大力擴張自己的買賣,拼命雇工啊! 在商賈們嘰嘰喳喳的議論中,刑恕騎著馬,在一隊禁軍的簇擁下,來到了這白馬鎮外的官道上,準備著歡迎遼使。 在他身邊,有一輛馬車,車上坐著耶律琚和耶律永昌。 “和叔……那位就是蕭德崇了……”耶律琚掀開車簾,看著出現在道路上,被宋軍簇擁著的遼國使團,指著在人群最前方的那位高大的遼國權貴說道:“其乃四國舅房的嫡脈所出,為人素來高傲……” 刑恕點點頭,作為大宋負責對外關系的大臣。 刑恕對遼國政治及其淵源,自然是用過功的。 何況,他還能從耶律琚和耶律永昌等人處了解、詢問。 故此他知道,不要看遼國后族,皆漢姓蕭氏,就以為他們系出同源。 但只要仔細研究,就會知道,漢姓蕭氏之外,遼國后族還有契丹姓氏。 而這些‘蕭姓’外戚的契丹姓氏,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一般來說,國舅家主要出自五個不同氏族,這就是遼人口中所謂的國舅五房了。 更正統的稱呼應該是:二國舅帳五房。 二國舅帳者,審密氏二姓,既契丹立國以前,還是部落聯盟時代,就專門和部落首領聯姻的審密氏拔里、乙室已兩族。 然而…… 其實,現在真正的審密氏拔里、乙室已兩族的人,早就被人殺光了。 遼國早期,混亂的政治,讓帝系都轉移了好幾次。 作為外戚的國舅帳,更是殺的人頭滾滾。 所以,現在的所謂二國舅帳五房,早不知道換了多少次血了。 蕭德崇所在的所謂國舅四房,就是承天太后時代才出現的乙室已少翁房。 這一房,系出承天太后父族蕭思溫家族——乃是蕭思溫幼子這一脈。 與如今遼國的后族,蕭思坦(廢皇后蕭觀音)所在的拔里氏國舅兩房,完全不是一個源頭——他們都是述律家族的后人。 當然,真述律還是假述律,就沒有人知道了。 刑恕遠遠的看著,那個騎在馬上,穿著遼國貴族服飾的中年男子,眼睛慢慢瞇起來:“高傲嗎?” 傲就傲吧! 當初,耶律琚入朝的時候,不也挺高傲的嗎? “他可有什么喜歡的我朝人物?”刑恕扭頭問道。 耶律琚想了想,答道:“據在下所知,此人不太喜好詩詞,倒是從小就喜歡聽人說蘇秦張儀的故事……” “蘇秦張儀?”刑恕咧嘴一笑:“吾也喜歡啊!” 他本來就是縱橫派,在被官家任用,主管大宋對外的外交后,就更喜歡了。 “待吾與之親近親近!” 喜歡蘇秦張儀好啊。 因為蘇秦張儀,從不在乎,自己給誰效力? 他們只在乎,誰會重用自己,以給自己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舞臺。 那蕭德崇在遼國,得到了他的舞臺嗎? 刑恕知道,至少現在還沒有。 不然他就不會這么默默無聞。 不然,就該是他坐在耶律琚和耶律永昌的所在的地方。 “蕭德崇旁的,就是張琳……此乃沈州人,少有大志,紛紛讀書,終中進士,為我主所愛……”耶律永昌從馬車里探出頭來,給刑恕介紹道:“此人,素以清流自居,好詩詞文章,乃是我大遼有名的詞臣。” 刑恕聽著,笑得更歡樂了。 好詩詞文章? 那他就來對地方了! 說話間,遠方官道上的遼使隊伍已經越來越近。 耶律琚和耶律永昌也就放下了車簾。 刑恕則翻身下馬,微笑著迎上前去,對著遼人使團隊伍,微微拱手一禮:“奉大宋皇帝陛下旨意,大宋翰林學士充館伴使刑恕,特來迎接諸位北國使臣!” 蕭德崇自然早早的看到了,在官道上的刑恕——刑恕穿著大宋的紫袍公服,頭戴著展腳幞頭,目標無比顯目,想不注意都難! 于是,他見到刑恕拱手,自也停下腳步,高舉代表大遼天子的節旄,微微欠身行禮:“奉大遼天子旨意,大遼崇儀軍節度使蕭德崇……” 與其并列而行,只是稍稍落后一個身位,穿著緋袍的張琳,也拱手問禮:“大遼中散大夫、充干文閣待制、守太常少卿張琳……” “特來恭賀大宋太皇太后坤寧圣節,以敘兩國兄弟之盟好!” 刑恕聽著,立刻再拱手,然后挺直腰桿,面朝皇城方向,鄭重的拿出一封敕書,抑揚頓挫的念了起來。 “卿久勤軺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這是學士院寫好的,用來宣讀給遼國使臣的慰勞敕書。 屬于是澶淵之盟的約定——兩國定期互遣使臣,修好交往,彼此使臣入境,自然要各頒詔書慰勉。 宋使入遼如此,遼使入宋亦如此。 在過去,這個程序是在遼使入境大宋的時候宣讀,所以叫‘茶馬敕’。 一般都是賜下茶水,以供遼使飲用、解渴、去乏。 并供給遼人草料,以便遼國使團的牲畜能補充一下體力。 但從去年開始,按照宋遼兩國的新約定。 降敕賜物的地點,從邊境改到了京城(皇帝捺缽所在)。 這是為了增進兩國的兄弟之盟。 同時,也是為了表達,兩國君主對兩國關系的重視——一入境就降下敕書,看似友好,實則在使團入境的時候,就會有著大量兵馬順勢將之保護起來。 如今,到京城(皇帝捺缽所在)附近,再降下敕書,就意味著,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彼此使團都能有一段相對輕松、自由的活動時間。 雖然說,依然是要在地方官監視下,走規定的路線。 但起碼,能夠近距離的觀察途徑地區的風土人情、地理地貌、交通河流。 而不是像囚犯一樣,一路被大批兵馬,死死圍住,恨不得連光都給使團遮住。 這是大宋方面開始自信的表現——過去,遼人其實無所謂宋庭使團在其境內怎么觀察風土人情、考察地理地貌、交通河流。 不然,大宋方面,也不會有那么多出使遼國的大臣能在回國后,寫下各種有關遼國的筆記甚至繪制出地圖。 對使團嚴防死守的,一直是大宋這邊。 畢竟,恐遼癥晚期患者,在大宋從宮中到朝中,從來不缺。 被遼人稍微恐嚇一下,就兩股瑟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甚至都不需要遼人恐嚇,自己就先亂了陣腳——比方說,造成了無數災難,使得數十軍州的數百萬百姓,在洪水中哀嚎的兩次回河,之所以會被推動,就是因為大宋方面,渴望黃河回到故道,擋住薛定諤的可能會從幽燕長驅直入的遼國鐵騎。 為此,郎心如鐵,哪怕撞得頭破血流,也依舊有無數人在為這個計劃癡迷。 我在現代留過學 第八百六十五章 遼使入京
休閑文學吧提供免費小說,請讀者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