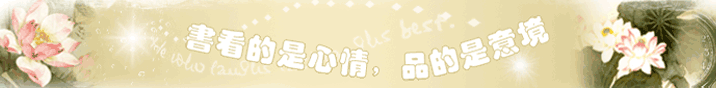第二百六十一章 處晦而觀明,守靜而制動
更新時間:2025-03-15 作者:趨時
大不列顛之影 第二百六十一章 處晦而觀明,守靜而制動
我肯定我們遲早有一天會因為印度而與俄國開戰。而我所擔心的是,直到希瓦被占領的那天我們都還蒙在鼓里。那么,俄國軍隊從希瓦開拔后三四個月就會抵達喀布爾。為了挫敗敵人的這一企圖,我們應當在敵人到達印度前就擊敗他們,否則等到兩萬俄軍到達印度后,就為時已晚了。不列顛已經無路可退,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俄國人阻擋在阿富汗,并為此制定一項捍衛中亞地區的前進政策。 ——威靈頓內閣時期,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埃倫伯勒勛爵 布萊克威爾近來一直覺得自己的上司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表現怪怪的。 如果說先前的亞瑟比起外交官更像是一名警察,那現在的亞瑟則顯然更符合布萊克威爾印象中的傳統外交官形象。 成天參加各種舞會和文學沙龍,不是在高級餐館與新結識的新朋友吃飯,就是在彼得堡的皇家劇院與各類社會名流小酌,甚至就連前往劇院的路上,他也不再翻閱那些枯燥無味的外交情報,而是捧起了俄國的文學雜志與法國的時裝雜志,時不時還要對各類文章與推薦穿搭評頭論足。 甚至于,爵士近來對女士們的興趣也正在急劇升高,這或許是因為他在某方面突然開了竅,嘗到了甜頭,又或許是他從哪位老前輩那里得知了“夫人外交”的妙處。 總而言之,最近的爵士實在是太反常了,就好像他真成了什么正經人物似的。 而這一切通通發生在爵士與那幾位大難不死的莫斯科年輕人會面之后。 雖然布萊克威爾不知道諢號“鐵心”的亞瑟是不是又被人用子彈開了竅,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亞瑟最近吩咐他干私活兒的頻率確實低了不少。 但是,工作量的驟然下降非但沒讓布萊克威爾感到高興,反倒使得這位私人秘書心中暗自惆悵。 難道是倫敦那邊出了什么變故? 爵士立功回倫敦的事情黃了? 布萊克威爾的心中惴惴不安,好在今早一封從倫敦寄來的信箋卻讓他重拾信心。 這些信箋外表雖然看起來平平無奇,但是上面眼花繚亂的頭銜卻使得布萊克威爾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 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切特豪斯公學校長、英格蘭首席治安官、倫敦塔總管、五港同盟總監、葡萄牙的維多利亞公爵、西班牙的首席大公羅德里戈公爵、尼德蘭王國與比利時王國的滑鐵盧親王…… 雖然信箋的主人開玩笑似的沒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取而代之的“法蘭西掘墓人”卻早就說明了他的身份——大不列顛的王下第一人威靈頓公爵。 雖然布萊克威爾早就聽說亞瑟與威靈頓公爵關系不錯,但是即便如此,當他看到亞瑟收到來自威靈頓公爵的親筆信時,依然不免感到震驚。 身為亞瑟的私人秘書,布萊克威爾甚至連捧著這封信都感覺到有種發自心底的榮幸。 “爵士……”布萊克威爾站在辦公桌的旁邊,望著坐在“惟吾德馨”書法下的亞瑟,小心翼翼地詢問道:“能否冒昧的問一句?公爵閣下給您寫信是倫敦出了什么事嗎?” 亞瑟叼著煙斗打量著書信,看都不看布萊克威爾一眼。 他嘴里碎碎念道:“倫敦哪天沒點事?只不過大部分事情都不值得公爵閣下關心罷了,他才懶得理會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自從不當首相之后,他老人家可是無事一身輕。” “既然如此……”難掩好奇心的布萊克威爾追問道:“那是為了什么事呢?總不能是拿破侖從棺材里揭竿而起了吧?” 亞瑟聞言情不自禁的想到了上個月路易在斯特拉斯堡發動政變遭到法國當局逮捕的事情,不得不說,路易模仿他叔叔的這場線下真人秀搞得相當失敗。 路易的這場政變幾乎可以與英國的光榮革命相媲美,它們的共同之處就在于二者都是不流血的。 是的,這場政變沒有一個人死亡,就連受傷的人數也不多,因此它即便失敗了,但也是存在閃光之處的。 就是不知道遠在南美的加里波第在得知路易政變的詳情后,會不會對他組織的那場糟糕的熱那亞起義感到釋懷。 雖然他們倆同樣考了不及格,但三十分和二十分還是存在區別的。 亞瑟一邊琢磨著他那群不靠譜的朋友們,嘴里也緊跟著脫口而出道:“無非就是一些政變……” “政變!”小秘書聽到這話嚇得臉都白了:“國……國內的局勢已經壞到這種程度了嗎?有人打算發動政變?” 亞瑟意識到他好像讓布萊克威爾產生了誤會,連忙改口道:“不是不列顛,而是印度,并且也不存在什么政變。” “印度?”布萊克威爾先是一愣,旋即忍不住喜上眉梢:“難道說,您要去……” 布萊克威爾話還沒說完,便立馬想起了亞瑟對于前往印度任職的態度,于是他趕忙壓住上翹的嘴角,在心中默想著已經去世的老祖母,擺出一副悲傷的姿態道:“威靈頓公爵都親自給您寫信了,看來事態的發展并不樂觀啊!我真是搞不懂,您剛剛妥善的處理好了高加索,然而他們居然打算派您去印度!那可是印度!文明人是不該去那種野蠻的次大陸的!” 亞瑟配合的皺起了眉頭,他輕輕搖了搖腦袋:“上命難違,雖然這確實很讓人傷腦筋,但是這畢竟是威靈頓公爵的意思。” “威靈頓公爵的意思?!”布萊克威爾驚呼道:“您……難道是孟買,抑或是馬德拉斯的省……” 到這里,他終于意識到自己好像太多嘴了,他趕忙閉上嘴巴,即便欣喜若狂的表情已經出賣了他。 但是沒過多久,前往那片香料之國的欲望便再次驅使著這位私人秘書動起了規勸上司“不要不知好歹”的心思:“爵士,其實細想想,這倒也不是個壞決定。雖然印度確實遠離本土,但是到東印度公司做事,也不代表您這輩子就被拴在印度了啊!畢竟東印度公司還有許多外派職位,比如東印度公司駐德黑蘭特使等等,這些職位雖然掛著東印度公司的名字,但是依然是屬于外交系統的,只要您干得好,返回歐洲那絕對是早晚的事。” 布萊克威爾滔滔不絕的向亞瑟講述著去印度的好處,而亞瑟深思的神情也仿佛像是被他說服了。 亞瑟將威靈頓公爵的來信擱在一邊,一只手托著下巴靠在辦公桌上:“好像確實是這么一回事。不過從俄國到印度,這一路上可要受不少累。” 布萊克威爾眼見有戲,趕忙趁熱打鐵道:“累不累得看您如何制定旅行計劃。威靈頓公爵不是曾經在印度任職多年嗎?他就沒有向您建議幾條舒適的路線?” 亞瑟翹著二郎腿抽了口煙:“公爵閣下確實提到了,他說以軍事家的角度來看,從俄國去印度有兩條陸路比較靠譜。第一條路線是先拿下希瓦,接著是巴爾赫,然后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翻越興都庫什山到達喀布爾。從那里,軍隊將經過賈拉拉巴德和開伯爾山口到達白沙瓦,最終在阿托克橫穿印度河。 他分析說,如果想奪取希瓦,最好是從奧倫堡而不是里海東岸發起進攻。這條線路雖然更遠,但水源狀況較卡拉庫姆沙漠要好很多,而且沿途的部落比起危險的土庫曼人來說也更容易制服。俄國軍隊抵達咸海北岸后,他們可以乘坐渡船或皮筏經水路到達阿姆河口,再南下直取希瓦。攻克希瓦繼而進軍印度是個極富野心的計劃,將會涉及一系列連續作戰,至少需要兩到三年時間才能完成。” 布萊克威爾越聽越感覺味道不對:“按制定軍事計劃的方式制定旅行路線,呃……不得不說,這很有名將的風格……” 亞瑟瞥了他一眼,接著補充道:“第二條可行的路線是先奪取赫拉特,然后以它為中轉站集結軍隊。從那里,部隊可以經坎大哈和奎達到達波倫山口,根據孟加拉地方第六輕騎兵團的康諾利中尉的探險報告,他就是經波倫山口到達印度的。而要想到達赫拉特,既可以選擇走陸路,經過已臣服于俄國的波斯,也可以橫跨里海到阿斯特拉巴德。因此,一旦阿富汗的赫拉特落入俄國手中,或者被與俄國交好的波斯吞并,那么俄國軍隊就可以輕而易舉在那里駐守多年,并可隨時獲得軍需用品。此時俄國人甚至不需要向印度挺進,因為俄國駐軍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擾亂到印度的本地民眾。而當不列顛面對印度可能發生的內亂時,就是俄國人發起進攻的絕佳時機。” “這……” 布萊克威爾就算再笨現在也明白亞瑟到底在打什么謎語了。 威靈頓公爵的這封信哪里是在給亞瑟下什么調職令? 這分明就是公爵閣下在擔心俄國人一旦控制中亞后,會謀求將他們的勢力范圍擴張到印度殖民地。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威靈頓公爵突然給身為英國駐俄文化參贊的亞瑟寫這么一封信,這背后隱藏的含義就很耐人尋味了。 布萊克威爾模糊的知道,在威靈頓公爵執政時期,鑒于奧斯曼和波斯都已經被俄國先后擊敗,并被裹脅簽訂了投降協議,威靈頓內閣十分擔心這兩個國家會成為俄國的附庸。為此,老公爵把他的好友兼托利黨鷹牌人物埃倫伯勒勛爵放到了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 埃倫伯勒勛爵是個堅定的反俄分子,并且他對俄國的擴張意圖始終堅信不疑。而隨著波斯被俄國擊敗,俄國的影響力在中亞地區持續擴大,東印度公司的幾個軍事探險隊甚至報告了在希瓦汗國目擊到俄國哥薩克活動的消息。 因此,埃倫伯勒勛爵擔心俄國人很可能會故技重施,先是俄國商人頻繁活動,俄國的軍隊則會緊隨商隊之后,以保護商旅安全為借口實施擴張。 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埃倫伯勒勛爵認為有理由詳細考察并繪制出俄國在中亞和北印度地區不斷延伸的商埠地圖,只要掌握了這些,就能監控俄國人進軍印度的路線。 為了達成這一目的,他煞費苦心的制定了一個不算光明正大的絕妙計策。 當時旁遮普國王蘭吉特·辛為了祝賀英國國王威廉四世登基,向他呈獻了一批華麗的克什米爾披肩,而威廉四世則在考慮該用什么東西來還禮。 根據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情報,這位年邁的印度王公鐘情女色,但這顯然不在考慮范圍內,因為不列顛本土現在可找不到女奴,即便政府可以找奧斯曼人買幾個現成的,但如果這事兒讓艦隊街的記者們知道了,那一準要鬧出大亂子。 除了女色之外,這位印度王公的另一項愛好是駿馬。 于是,埃倫伯勒勛爵便萌生了一個想法。 他計劃送給蘭吉特·辛五匹英國純血馬,其中包括四匹母馬和一匹種馬。 作為一種從17世紀為了賽馬專門培育的馬種,英國純血馬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中短距離最快的馬種。考慮到這位亞洲君主最近曾派遣特使去圣彼得堡,埃倫伯勒勛爵希望能用這幾匹足以在德比馬賽上取得優勝的英國純血馬能夠打動旁遮普國王。 與此同時,他還命令孟買總督約翰·馬爾科姆爵士建造一駕鍍金的慶典馬車,屆時蘭吉特·辛就可以坐在由英國駿馬牽引的豪華馬車里,舒適而威嚴地巡視他的王國了。 當然,這肯定不是計劃的全部。 由于馬匹和馬車的體量巨大,而且馬匹不適應當地氣候和地勢,它們恐怕無法經陸路跋涉抵達旁遮普王國的首都拉合爾。因此,英國提出需要取道水路沿印度河逆流而上的要求就變得順理成章,對河道進行詳細勘察以確保水運可以直通拉合爾也顯得合情合理了。 但遺憾的是,埃倫伯勒勛爵的天才計劃遭到了東印度公司機密政治部秘書長查爾斯·梅特卡夫爵士的堅決反對,他認為印度王公原本就因為一些類似的詭計錯怪英國政府,況且這個偵查計劃極易被覺察,到時候只會更加加深本地君主對英國的誤會。 不過孟買省督約翰·馬爾科姆爵士倒是非常支持埃倫伯勒勛爵的想法,并且認為為了防止俄國對印度的威脅,必須得制定一項前進政策,因為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然而就在這項計劃即將拍板的時候,威靈頓公爵因為《天主教解放法案》被趕下了臺,而與老伙計同進退的埃倫伯勒勛爵也隨之離開了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孟買省督馬爾科姆爵士擔心日久生變,于是快刀斬亂麻,立刻催促探險隊出發。 探險隊于1831年1月出發,1833年3月返回孟買。 之所以這場探險持續了這么長時間,主要是因為探險隊隊長印度政治服務精銳團的伯恩斯中尉不僅向旁遮普國王進獻了駿馬和馬車,還獲得了馬爾科姆爵士的認可,并自告奮勇的主動要求穿過旁遮普勘察其他至今未被發現的入印道路。 伯恩斯中尉一行人脫掉歐洲服飾,換上阿富汗服裝,剃光頭發,纏上頭巾,偽裝成英國旅行者,一路向北進入阿富汗地區,并在喀布爾見到了阿富汗地區最強大的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 在雙方熟絡起來之后,穆罕默德甚至主動提出請伯恩斯出任他的軍事訓練指揮官,向伯恩斯許諾說:“由你來掌管一萬兩千匹馬和二十門炮。” 即便伯恩斯拒絕了這個提議,可穆罕默德依然不死心的希望他能夠幫忙推薦東印度公司的其他軍官來擔任這一職務。 之所以這位阿富汗君主這么渴望由外國人來訓練他的軍隊,這還得談起那位旁遮普國王蘭吉特·辛。在過去的數百年當中,阿富汗人都可以通過開伯爾山口涌入印度,洗劫德里,然后再帶著大批金銀財寶滿載而歸。 可是自從印度王公開始聘請歐洲軍官團來訓練改造他們的軍隊以后,阿富汗人就再也沒過上從前的好日子了。 而伯恩斯拒絕穆罕默德倒也不是他不愿意接受這個飛黃騰達的機會,而是不列顛與蘭吉特·辛簽有長期合作協議,如果他敢接這種私活,那這輩子基本不用指望再回英國了。 伯恩斯中尉今年才26歲,而且剛剛才完成了探險任務,眼前擺著明晃晃的光明前途,他怎么可能為了一個在印度作威作福的機會便拋棄了在不列顛揚名立萬的機會呢? 而且,比起挑起阿富汗人與旁遮普人的戰爭,進而導致俄國人趁虛而入,顯然是讓他們和平相處更符合英國的利益。 讓阿富汗人與鄰居和平相處是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要重新整合分裂的阿富汗,幫助他們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政權,以防備隨時可能出現的俄國入侵風險。 至于究竟讓誰來當這個阿富汗話事人,伯恩斯中尉當然力挺喀布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 但不幸的是,穆罕默德并不是唯一候選人,控制了赫拉特的卡姆蘭也是重點觀察對象。 這是由于早在伯恩斯中尉之前,東印度公司的康諾特中尉就曾經造訪過阿富汗地區,而赫拉特則是他認為的軍事要地。 說起康諾特中尉的這段經歷,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段傳奇游記。 1831年的時候,康諾特中尉剛剛在莫斯科結束假期,計劃返回印度工作。 由于他的身份,在康諾特穿越危險的高加索地區時,俄國政府還熱情的專門派了哥薩克騎兵保護他。 而在抵達波斯后,突發奇想的康諾特居然沒有選擇經過海路回到印度,而是選擇穿越沙漠和阿富汗的高原走一條前人不曾走過的路。 康諾特在這一路上幾度遭遇生命危險,遇到過攔路搶劫的土匪,也碰見過奴隸販子的獵奴隊,還差點被正在交戰的阿富汗軍閥懷疑為敵對勢力的間諜,在到達印度的前幾天還差點死于高燒。 而他也終于意識到為什么他走的路前人沒有走過了,那是因為走過的前人大多都死在半道上了。 不過,好在他完成了這一長達四千英里的旅途,并用時三年將這一傳奇經歷寫成了一本名為《從英國陸路出發前往印度以北地區,途經俄國、波斯及阿富汗》的小冊子。 更令人欣喜的是,一直苦于沒有資金出版的康諾特中尉前不久在倫敦遇上了熱情的《英國佬》雜志社編輯,對方不僅十分欣賞康諾特的作品、答應出版他的書,甚至還給出了一筆數目可觀的價格。 當然了,給這么多錢,肯定不是毫無條件的。 只不過這個條件在康諾特看來簡直稱不上是什么要求,對方只是希望:在詳細分析可供俄國將軍選擇的入侵印度的路線和各種入侵計劃成功可能性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夸張。 對于出版商來說,這樣的要求合情合理,畢竟只有這么寫才能有噱頭,而噱頭則直接關系到銷量的多少。 康諾特對此自然是欣然接受。 只不過康諾特顯然沒有料到這部書在出版后居然會如此成功,甚至于威靈頓公爵都在黨內新秀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推薦下認真的研讀了他的分析結果。 本就憂心忡忡的威靈頓公爵在讀完這本書后徹夜難眠,以致于想起了幾周前駐俄文化參贊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從彼得堡發來的隱晦指責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子爵對俄態度軟弱的外交報告。 為此,閑不住的老公爵立馬派人去外交部要求調取近期關于高加索地區情勢分析的外交報告。 結果可想而知,這些外交報告當中有一多半都是出自亞瑟的手筆,而上面的觀點幾乎處處印證了康諾特中尉的觀察和推測。 于是,威靈頓公爵大手一揮,親筆信便漂洋過海的來到了彼得堡的英國使館辦公桌。 大不列顛之影 第二百六十一章 處晦而觀明,守靜而制動
我肯定我們遲早有一天會因為印度而與俄國開戰。而我所擔心的是,直到希瓦被占領的那天我們都還蒙在鼓里。那么,俄國軍隊從希瓦開拔后三四個月就會抵達喀布爾。為了挫敗敵人的這一企圖,我們應當在敵人到達印度前就擊敗他們,否則等到兩萬俄軍到達印度后,就為時已晚了。不列顛已經無路可退,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俄國人阻擋在阿富汗,并為此制定一項捍衛中亞地區的前進政策。 ——威靈頓內閣時期,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埃倫伯勒勛爵 布萊克威爾近來一直覺得自己的上司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表現怪怪的。 如果說先前的亞瑟比起外交官更像是一名警察,那現在的亞瑟則顯然更符合布萊克威爾印象中的傳統外交官形象。 成天參加各種舞會和文學沙龍,不是在高級餐館與新結識的新朋友吃飯,就是在彼得堡的皇家劇院與各類社會名流小酌,甚至就連前往劇院的路上,他也不再翻閱那些枯燥無味的外交情報,而是捧起了俄國的文學雜志與法國的時裝雜志,時不時還要對各類文章與推薦穿搭評頭論足。 甚至于,爵士近來對女士們的興趣也正在急劇升高,這或許是因為他在某方面突然開了竅,嘗到了甜頭,又或許是他從哪位老前輩那里得知了“夫人外交”的妙處。 總而言之,最近的爵士實在是太反常了,就好像他真成了什么正經人物似的。 而這一切通通發生在爵士與那幾位大難不死的莫斯科年輕人會面之后。 雖然布萊克威爾不知道諢號“鐵心”的亞瑟是不是又被人用子彈開了竅,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亞瑟最近吩咐他干私活兒的頻率確實低了不少。 但是,工作量的驟然下降非但沒讓布萊克威爾感到高興,反倒使得這位私人秘書心中暗自惆悵。 難道是倫敦那邊出了什么變故? 爵士立功回倫敦的事情黃了? 布萊克威爾的心中惴惴不安,好在今早一封從倫敦寄來的信箋卻讓他重拾信心。 這些信箋外表雖然看起來平平無奇,但是上面眼花繚亂的頭銜卻使得布萊克威爾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 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切特豪斯公學校長、英格蘭首席治安官、倫敦塔總管、五港同盟總監、葡萄牙的維多利亞公爵、西班牙的首席大公羅德里戈公爵、尼德蘭王國與比利時王國的滑鐵盧親王…… 雖然信箋的主人開玩笑似的沒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取而代之的“法蘭西掘墓人”卻早就說明了他的身份——大不列顛的王下第一人威靈頓公爵。 雖然布萊克威爾早就聽說亞瑟與威靈頓公爵關系不錯,但是即便如此,當他看到亞瑟收到來自威靈頓公爵的親筆信時,依然不免感到震驚。 身為亞瑟的私人秘書,布萊克威爾甚至連捧著這封信都感覺到有種發自心底的榮幸。 “爵士……”布萊克威爾站在辦公桌的旁邊,望著坐在“惟吾德馨”書法下的亞瑟,小心翼翼地詢問道:“能否冒昧的問一句?公爵閣下給您寫信是倫敦出了什么事嗎?” 亞瑟叼著煙斗打量著書信,看都不看布萊克威爾一眼。 他嘴里碎碎念道:“倫敦哪天沒點事?只不過大部分事情都不值得公爵閣下關心罷了,他才懶得理會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自從不當首相之后,他老人家可是無事一身輕。” “既然如此……”難掩好奇心的布萊克威爾追問道:“那是為了什么事呢?總不能是拿破侖從棺材里揭竿而起了吧?” 亞瑟聞言情不自禁的想到了上個月路易在斯特拉斯堡發動政變遭到法國當局逮捕的事情,不得不說,路易模仿他叔叔的這場線下真人秀搞得相當失敗。 路易的這場政變幾乎可以與英國的光榮革命相媲美,它們的共同之處就在于二者都是不流血的。 是的,這場政變沒有一個人死亡,就連受傷的人數也不多,因此它即便失敗了,但也是存在閃光之處的。 就是不知道遠在南美的加里波第在得知路易政變的詳情后,會不會對他組織的那場糟糕的熱那亞起義感到釋懷。 雖然他們倆同樣考了不及格,但三十分和二十分還是存在區別的。 亞瑟一邊琢磨著他那群不靠譜的朋友們,嘴里也緊跟著脫口而出道:“無非就是一些政變……” “政變!”小秘書聽到這話嚇得臉都白了:“國……國內的局勢已經壞到這種程度了嗎?有人打算發動政變?” 亞瑟意識到他好像讓布萊克威爾產生了誤會,連忙改口道:“不是不列顛,而是印度,并且也不存在什么政變。” “印度?”布萊克威爾先是一愣,旋即忍不住喜上眉梢:“難道說,您要去……” 布萊克威爾話還沒說完,便立馬想起了亞瑟對于前往印度任職的態度,于是他趕忙壓住上翹的嘴角,在心中默想著已經去世的老祖母,擺出一副悲傷的姿態道:“威靈頓公爵都親自給您寫信了,看來事態的發展并不樂觀啊!我真是搞不懂,您剛剛妥善的處理好了高加索,然而他們居然打算派您去印度!那可是印度!文明人是不該去那種野蠻的次大陸的!” 亞瑟配合的皺起了眉頭,他輕輕搖了搖腦袋:“上命難違,雖然這確實很讓人傷腦筋,但是這畢竟是威靈頓公爵的意思。” “威靈頓公爵的意思?!”布萊克威爾驚呼道:“您……難道是孟買,抑或是馬德拉斯的省……” 到這里,他終于意識到自己好像太多嘴了,他趕忙閉上嘴巴,即便欣喜若狂的表情已經出賣了他。 但是沒過多久,前往那片香料之國的欲望便再次驅使著這位私人秘書動起了規勸上司“不要不知好歹”的心思:“爵士,其實細想想,這倒也不是個壞決定。雖然印度確實遠離本土,但是到東印度公司做事,也不代表您這輩子就被拴在印度了啊!畢竟東印度公司還有許多外派職位,比如東印度公司駐德黑蘭特使等等,這些職位雖然掛著東印度公司的名字,但是依然是屬于外交系統的,只要您干得好,返回歐洲那絕對是早晚的事。” 布萊克威爾滔滔不絕的向亞瑟講述著去印度的好處,而亞瑟深思的神情也仿佛像是被他說服了。 亞瑟將威靈頓公爵的來信擱在一邊,一只手托著下巴靠在辦公桌上:“好像確實是這么一回事。不過從俄國到印度,這一路上可要受不少累。” 布萊克威爾眼見有戲,趕忙趁熱打鐵道:“累不累得看您如何制定旅行計劃。威靈頓公爵不是曾經在印度任職多年嗎?他就沒有向您建議幾條舒適的路線?” 亞瑟翹著二郎腿抽了口煙:“公爵閣下確實提到了,他說以軍事家的角度來看,從俄國去印度有兩條陸路比較靠譜。第一條路線是先拿下希瓦,接著是巴爾赫,然后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翻越興都庫什山到達喀布爾。從那里,軍隊將經過賈拉拉巴德和開伯爾山口到達白沙瓦,最終在阿托克橫穿印度河。 他分析說,如果想奪取希瓦,最好是從奧倫堡而不是里海東岸發起進攻。這條線路雖然更遠,但水源狀況較卡拉庫姆沙漠要好很多,而且沿途的部落比起危險的土庫曼人來說也更容易制服。俄國軍隊抵達咸海北岸后,他們可以乘坐渡船或皮筏經水路到達阿姆河口,再南下直取希瓦。攻克希瓦繼而進軍印度是個極富野心的計劃,將會涉及一系列連續作戰,至少需要兩到三年時間才能完成。” 布萊克威爾越聽越感覺味道不對:“按制定軍事計劃的方式制定旅行路線,呃……不得不說,這很有名將的風格……” 亞瑟瞥了他一眼,接著補充道:“第二條可行的路線是先奪取赫拉特,然后以它為中轉站集結軍隊。從那里,部隊可以經坎大哈和奎達到達波倫山口,根據孟加拉地方第六輕騎兵團的康諾利中尉的探險報告,他就是經波倫山口到達印度的。而要想到達赫拉特,既可以選擇走陸路,經過已臣服于俄國的波斯,也可以橫跨里海到阿斯特拉巴德。因此,一旦阿富汗的赫拉特落入俄國手中,或者被與俄國交好的波斯吞并,那么俄國軍隊就可以輕而易舉在那里駐守多年,并可隨時獲得軍需用品。此時俄國人甚至不需要向印度挺進,因為俄國駐軍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擾亂到印度的本地民眾。而當不列顛面對印度可能發生的內亂時,就是俄國人發起進攻的絕佳時機。” “這……” 布萊克威爾就算再笨現在也明白亞瑟到底在打什么謎語了。 威靈頓公爵的這封信哪里是在給亞瑟下什么調職令? 這分明就是公爵閣下在擔心俄國人一旦控制中亞后,會謀求將他們的勢力范圍擴張到印度殖民地。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威靈頓公爵突然給身為英國駐俄文化參贊的亞瑟寫這么一封信,這背后隱藏的含義就很耐人尋味了。 布萊克威爾模糊的知道,在威靈頓公爵執政時期,鑒于奧斯曼和波斯都已經被俄國先后擊敗,并被裹脅簽訂了投降協議,威靈頓內閣十分擔心這兩個國家會成為俄國的附庸。為此,老公爵把他的好友兼托利黨鷹牌人物埃倫伯勒勛爵放到了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 埃倫伯勒勛爵是個堅定的反俄分子,并且他對俄國的擴張意圖始終堅信不疑。而隨著波斯被俄國擊敗,俄國的影響力在中亞地區持續擴大,東印度公司的幾個軍事探險隊甚至報告了在希瓦汗國目擊到俄國哥薩克活動的消息。 因此,埃倫伯勒勛爵擔心俄國人很可能會故技重施,先是俄國商人頻繁活動,俄國的軍隊則會緊隨商隊之后,以保護商旅安全為借口實施擴張。 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埃倫伯勒勛爵認為有理由詳細考察并繪制出俄國在中亞和北印度地區不斷延伸的商埠地圖,只要掌握了這些,就能監控俄國人進軍印度的路線。 為了達成這一目的,他煞費苦心的制定了一個不算光明正大的絕妙計策。 當時旁遮普國王蘭吉特·辛為了祝賀英國國王威廉四世登基,向他呈獻了一批華麗的克什米爾披肩,而威廉四世則在考慮該用什么東西來還禮。 根據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情報,這位年邁的印度王公鐘情女色,但這顯然不在考慮范圍內,因為不列顛本土現在可找不到女奴,即便政府可以找奧斯曼人買幾個現成的,但如果這事兒讓艦隊街的記者們知道了,那一準要鬧出大亂子。 除了女色之外,這位印度王公的另一項愛好是駿馬。 于是,埃倫伯勒勛爵便萌生了一個想法。 他計劃送給蘭吉特·辛五匹英國純血馬,其中包括四匹母馬和一匹種馬。 作為一種從17世紀為了賽馬專門培育的馬種,英國純血馬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中短距離最快的馬種。考慮到這位亞洲君主最近曾派遣特使去圣彼得堡,埃倫伯勒勛爵希望能用這幾匹足以在德比馬賽上取得優勝的英國純血馬能夠打動旁遮普國王。 與此同時,他還命令孟買總督約翰·馬爾科姆爵士建造一駕鍍金的慶典馬車,屆時蘭吉特·辛就可以坐在由英國駿馬牽引的豪華馬車里,舒適而威嚴地巡視他的王國了。 當然,這肯定不是計劃的全部。 由于馬匹和馬車的體量巨大,而且馬匹不適應當地氣候和地勢,它們恐怕無法經陸路跋涉抵達旁遮普王國的首都拉合爾。因此,英國提出需要取道水路沿印度河逆流而上的要求就變得順理成章,對河道進行詳細勘察以確保水運可以直通拉合爾也顯得合情合理了。 但遺憾的是,埃倫伯勒勛爵的天才計劃遭到了東印度公司機密政治部秘書長查爾斯·梅特卡夫爵士的堅決反對,他認為印度王公原本就因為一些類似的詭計錯怪英國政府,況且這個偵查計劃極易被覺察,到時候只會更加加深本地君主對英國的誤會。 不過孟買省督約翰·馬爾科姆爵士倒是非常支持埃倫伯勒勛爵的想法,并且認為為了防止俄國對印度的威脅,必須得制定一項前進政策,因為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然而就在這項計劃即將拍板的時候,威靈頓公爵因為《天主教解放法案》被趕下了臺,而與老伙計同進退的埃倫伯勒勛爵也隨之離開了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孟買省督馬爾科姆爵士擔心日久生變,于是快刀斬亂麻,立刻催促探險隊出發。 探險隊于1831年1月出發,1833年3月返回孟買。 之所以這場探險持續了這么長時間,主要是因為探險隊隊長印度政治服務精銳團的伯恩斯中尉不僅向旁遮普國王進獻了駿馬和馬車,還獲得了馬爾科姆爵士的認可,并自告奮勇的主動要求穿過旁遮普勘察其他至今未被發現的入印道路。 伯恩斯中尉一行人脫掉歐洲服飾,換上阿富汗服裝,剃光頭發,纏上頭巾,偽裝成英國旅行者,一路向北進入阿富汗地區,并在喀布爾見到了阿富汗地區最強大的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 在雙方熟絡起來之后,穆罕默德甚至主動提出請伯恩斯出任他的軍事訓練指揮官,向伯恩斯許諾說:“由你來掌管一萬兩千匹馬和二十門炮。” 即便伯恩斯拒絕了這個提議,可穆罕默德依然不死心的希望他能夠幫忙推薦東印度公司的其他軍官來擔任這一職務。 之所以這位阿富汗君主這么渴望由外國人來訓練他的軍隊,這還得談起那位旁遮普國王蘭吉特·辛。在過去的數百年當中,阿富汗人都可以通過開伯爾山口涌入印度,洗劫德里,然后再帶著大批金銀財寶滿載而歸。 可是自從印度王公開始聘請歐洲軍官團來訓練改造他們的軍隊以后,阿富汗人就再也沒過上從前的好日子了。 而伯恩斯拒絕穆罕默德倒也不是他不愿意接受這個飛黃騰達的機會,而是不列顛與蘭吉特·辛簽有長期合作協議,如果他敢接這種私活,那這輩子基本不用指望再回英國了。 伯恩斯中尉今年才26歲,而且剛剛才完成了探險任務,眼前擺著明晃晃的光明前途,他怎么可能為了一個在印度作威作福的機會便拋棄了在不列顛揚名立萬的機會呢? 而且,比起挑起阿富汗人與旁遮普人的戰爭,進而導致俄國人趁虛而入,顯然是讓他們和平相處更符合英國的利益。 讓阿富汗人與鄰居和平相處是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要重新整合分裂的阿富汗,幫助他們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政權,以防備隨時可能出現的俄國入侵風險。 至于究竟讓誰來當這個阿富汗話事人,伯恩斯中尉當然力挺喀布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 但不幸的是,穆罕默德并不是唯一候選人,控制了赫拉特的卡姆蘭也是重點觀察對象。 這是由于早在伯恩斯中尉之前,東印度公司的康諾特中尉就曾經造訪過阿富汗地區,而赫拉特則是他認為的軍事要地。 說起康諾特中尉的這段經歷,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段傳奇游記。 1831年的時候,康諾特中尉剛剛在莫斯科結束假期,計劃返回印度工作。 由于他的身份,在康諾特穿越危險的高加索地區時,俄國政府還熱情的專門派了哥薩克騎兵保護他。 而在抵達波斯后,突發奇想的康諾特居然沒有選擇經過海路回到印度,而是選擇穿越沙漠和阿富汗的高原走一條前人不曾走過的路。 康諾特在這一路上幾度遭遇生命危險,遇到過攔路搶劫的土匪,也碰見過奴隸販子的獵奴隊,還差點被正在交戰的阿富汗軍閥懷疑為敵對勢力的間諜,在到達印度的前幾天還差點死于高燒。 而他也終于意識到為什么他走的路前人沒有走過了,那是因為走過的前人大多都死在半道上了。 不過,好在他完成了這一長達四千英里的旅途,并用時三年將這一傳奇經歷寫成了一本名為《從英國陸路出發前往印度以北地區,途經俄國、波斯及阿富汗》的小冊子。 更令人欣喜的是,一直苦于沒有資金出版的康諾特中尉前不久在倫敦遇上了熱情的《英國佬》雜志社編輯,對方不僅十分欣賞康諾特的作品、答應出版他的書,甚至還給出了一筆數目可觀的價格。 當然了,給這么多錢,肯定不是毫無條件的。 只不過這個條件在康諾特看來簡直稱不上是什么要求,對方只是希望:在詳細分析可供俄國將軍選擇的入侵印度的路線和各種入侵計劃成功可能性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夸張。 對于出版商來說,這樣的要求合情合理,畢竟只有這么寫才能有噱頭,而噱頭則直接關系到銷量的多少。 康諾特對此自然是欣然接受。 只不過康諾特顯然沒有料到這部書在出版后居然會如此成功,甚至于威靈頓公爵都在黨內新秀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推薦下認真的研讀了他的分析結果。 本就憂心忡忡的威靈頓公爵在讀完這本書后徹夜難眠,以致于想起了幾周前駐俄文化參贊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從彼得堡發來的隱晦指責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子爵對俄態度軟弱的外交報告。 為此,閑不住的老公爵立馬派人去外交部要求調取近期關于高加索地區情勢分析的外交報告。 結果可想而知,這些外交報告當中有一多半都是出自亞瑟的手筆,而上面的觀點幾乎處處印證了康諾特中尉的觀察和推測。 于是,威靈頓公爵大手一揮,親筆信便漂洋過海的來到了彼得堡的英國使館辦公桌。 大不列顛之影 第二百六十一章 處晦而觀明,守靜而制動
休閑文學吧提供免費小說,請讀者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