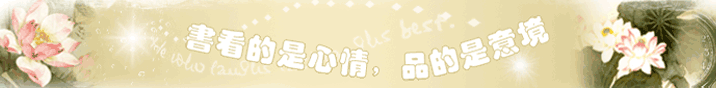第八百六十八章 利益關系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更新時間:2025-04-02 作者:吾誰與歸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八百六十八章 利益關系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鈞雖然把兗州孔府的根兒都拔了,但他其實不反對儒學,甚至覺得孔子、孟子,很多四書五經講的很有道理。 即便是萬歷維新浩浩蕩蕩,大明的丁亥學制,并沒有拋棄儒學,因為儒學里面有很多的內容,也是值得借鑒的,無論是個人的修身,還是國朝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比如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也就是朱翊鈞所說的,國朝最為危險的就是鮮花錦簇日,歌舞升平時。 如果沒有任何的危機意識,國家滅亡就是必然的,作為統治階級,不能沉湎于鮮花錦簇和歌舞升平,而是應該看到水面下暗流涌動的危機。 因為一旦沉湎于鮮花錦簇和歌舞升平,就必然會帶來一個可怕的結果,那就是飾勝,把一切的一切都包裝成為勝利,輸也能變成贏,最終在不斷的贏贏贏的掌聲中,走向滅亡。 大明在晚明到南明這段時間,就充斥著這種贏贏贏的風潮,闖王李自成被剿滅了數次,最慘烈的時候,身邊就只有二十一人,但很快他就再次拉起了百萬的農民軍,把大明王朝給斷了。 崇禎九年,第一代闖王高迎祥被剿滅,高迎祥被拉到京師凌遲處死,這對大明而言是巨大的勝利,從萬歷末年開始的陜甘寧三地的民亂,看似是畫上了一個句號。 崇禎皇帝贏了,但其實也沒有真正的勝利,因為他沒有解決民亂爆發的根本誘因。 朝廷欠餉,讓三邊軍屯衛所的基層軍官都開始逃離衛所,加入了農民軍成為了基層的組織者,讓農民軍有了正面對抗官軍的實力; 其次,陜甘寧三邊大旱,沒有糧食賑濟災民,無窮無盡走投無路的百姓,只能跟隨闖王。 最重要的還是人地矛盾,自萬歷十年張居正離世后,天下再無人敢抑制兼并,因為地主官僚階級對張居正為首的張黨,展開了最深入的清算,任何和張居正有一點關系的人,都要被徹底打倒,地主官僚階級勝利了,再沒人敢抑制兼并了。 消滅農民軍對于大明官軍而言不是難事,一直到崇禎十五年,大明官軍對農民軍依舊是優勢,洪承疇對農民軍幾乎完勝,但贏,已經沒什么用了,可是如何讓百姓安頓下來,不再成為農民軍的兵源,才是最大的矛盾。 而矛盾說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觀察問題的方法論,現象、問題、原因、方案、實踐、修正、再推行、再修正,這一套的方法論,無往不利。 大明贏學要真的贏,要建立在矛盾說的基礎上、建立在華夷之辯的基礎上,而不是飾勝。 大明士大夫普遍可以接受在陽明心學上建立的矛盾說,也可以接受在華夷之辯、矛盾說上建立的大明贏學,而不是蠻夷飾勝贏學。 但大明士大夫階級,其實真的很難以接受階級論。 大明士大夫在大明思辨成果文集的傳播過程中,對矛盾說的注釋進行自己注解,但對階級論則采用刪減、修改的方法,來對抗階級論的傳播。 在許多讀書人的眼里,矛盾說很好,甚至值得深入討論,可階級論得看統治者是否認可。 張居正寫出第二卷分配,就直接燒了,不是皇帝挽救及時,根本不會刊行。 而階級論第三卷干脆就是朱翊鈞寫的了,連張居正這個革故鼎新的改革家、變法者,都難以接受第二卷,更別說第三卷了。 朱翊鈞和袁可立伸出了同樣的手,就是告訴袁可立,他的立場,他們在志向上相同,在行為上相同,在階級認同上相同,同志同行則同樂者。 “陸樹聲到全楚會館索人,朕不認可,他自己選擇私門小利,以個人利益為首,那是他的自由,自私在朕看來,是個中性的詞,人不自私,那就不是人了。”朱翊鈞頗為確切地說道:“但他不能以自己的行為標準,去要求別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兒,也不要強加于他人,這句話強調的是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的那套利己思維,強加于別人身上,這才是有修養,人和人各有不同。 “先生主要是擔心袁可立沒有人給他撐腰,扛不住一些風波。”熊廷弼為張居正說了句好話,殿試之后,單獨宣見了兩名學子,這是告訴天下人,袁可立是皇帝罩著,可之前袁可立可沒這等殊榮。 人要活在現實里,自己承擔不了的風波,要極力去避免,那不是迎難而上,而是找死。 “現在有人給禮卿撐腰了。”朱翊鈞當然清楚張居正的擔心,怕百年之后,袁可立還沒成長起來,沒有保護自己的力量。 拜師陸樹聲,做個看起來有點傳統的讀書人,對于袁可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否則他就不會罵萬歷皇帝了,還罵的那么難聽。 朱翊鈞看著袁可立說道:“禮卿會試的文章,朕看了,你的文章寫的很好,六千舉人,只有七十份說了這萬歷維新的弊端。” 袁可立在歌功頌德和針砭時事上選擇了后者,他其實早就做出了選擇,而不是陸樹聲上門,才做了選擇。 貢院會試多了一個規矩,因為是皇帝發考籃,所以所有的草稿紙張,不得帶出考場、不準丟棄,而緹騎會將每一張草稿紙收集起來,對每一名中式貢士進行核驗,防止弄虛作假。 搜檢懷挾官仍然常設,因為有些人會把夾帶藏進谷道里,雖然非常惡心,但確實發生過,這塞進谷道里,總不能是有人栽贓嫁禍了。 在搜檢之外,現在會試,多了一套驗證的程序,沒有人的文章是一氣呵成的,尤其是這會試,需要多次謄抄,力求寫到完美,那么草稿紙,就成為了核驗的重要工具。 等到確定無誤后,這些草稿紙會被打碎放入池子中,放入白土漂白后,再次做成紙張。 浪費是極其可恥的。 因為有核驗的程序,所以袁可立寫了一篇錦繡文章,修改好了,最終卻選擇了針砭時事,這是勇氣。 而袁可立的文章寫的極好,主要是萬歷維新的新政,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新政在河南地方是非常成功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 袁可立從河南本身出發,探討了內陸地區的發展困境。 大明已經形成了一種路徑上的依賴,大明貧銀貧銅、內部貨幣錢荒、內部需求不足、海外有金銀銅、產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大規模生產用商品換到貴金屬、再投入擴大再生產、而后逐步輻射腹地。 這種路徑有兩個巨大的弊病。 第一個生產再擴大仍然在滿足外部需求,而非內部,甚至因為外部需求不夠旺盛,陷入了惡性競爭的困局之中,擴大后的生產,并沒有逐步輻射到腹地。 造成這種原因也簡單,內地的錢荒問題,沒有根本性改變; 這個弊病是極為可怕的,因為無法完成內需的建設,大明空有商品優勢,完全無法發揮商品經濟的優勢,從海貿中,獲取更多超額的利潤的同時,還會增加離心力。 價值受勞動強度、勞動時間、勞動難度影響,而價格圍繞著價值、供需、成本進行波動,這是生產圖說里關于價值和價格的討論。 大明沿海地區產業豐富,大明內部無法消化,就得依靠外部需求,這個時候,主動權就交給對方。 這就走入了一個怪圈,產業越豐富,越密集,越要壓價,利潤降低,越不賺錢的困境。 大明是個整體,但兩京一十五省五大總督府,也有個嫡庶之分,在重大危機面前,還有可能各地趨同,可是涉及到了各種細分的產業利益瓜分,親兄弟也要明算賬的。 如何在萬歷維新中,保證向心力,不因為利益分配的問題分家,是朝廷必須要考慮清楚的。 簡單而言,就是外向型經濟,造成的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內需建設不充分導致內需不足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影響國朝根本。 第二個問題,就是老生常談的人口流失、人口不足的問題了,而袁可立用一句俗語,解釋了這個現象背后折射的問題:窮的不生,中人之家也不生; 原因也簡單:干活的時候嫌人少,吃飯的時候嫌人多。 窮是討不到媳婦,就是討得到,生出來養不起,所以不生,但中人之家,也不生,就非常詭異了,大明很多的中人之家,即便是有了孩子也會溺死,不是養不起,而是供不起。 大明天下,窮人和中人之家占據了絕對的多數,他們不生,大富大貴、頂層向下開枝散葉,又能生幾個?王崇古家里足夠有錢,他就兩個兒子,還有一個英年早逝,留下一個王謙,而王謙一共就兩個兒子,兩個閨女,說什么也不肯生了。 而袁可立在會試的文章里分析了問題的癥結。 小到一個家庭,大到大明江山,都是如此。 干活的時候,希望人多多的,一起創造財富,等到分配的時候,又開始嫌吃飯的人多,即便在鄉野之間,耕種農桑最需要勞力,可是一個勞力從小到大,吃的又多了。 袁可立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談,絲毫沒有露出任何怯懦,將自己的想法解釋的非常清楚。 對第一個問題,他提出了三個主要解決的辦法,大建馳道進行分配、黃河歸故讓兩淮地區擺脫黃河帶來的困擾、而后疏浚淮河、長江,讓沿海的富裕順著大江大河馳道,向腹地輻射。 當然這都是遠景規劃,現在大明的生產力,還是對黃河有些無能為力,讓黃河歸故才能疏浚淮河,讓長江黃河流域,輻射到大明大部分地區,沒有大江大河的地方,則依托于馳道。 這個思路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時間尺度在百年之上。 第二個問題,則主要聚焦于田政之上,清丈還田、營莊減租,四管齊下,期許在有生之年,能夠徹底執行下去,最終奠定了萬歷盛世的堅實根基。 相比較還田,袁可立更加推崇營莊法。 在他看來,還田之后,這些田土最后還是會被兼并,營莊集體所有,反而會讓鄉野之間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大富大貴不敢想,但吃得上飯還是可以期許的。 朱翊鈞叫袁可立入通和宮,其實沒什么正事,就是一種立場宣示,他就是個學生,經驗不足,討論的內容,十分的空洞,他需要不斷的成長,在實踐中不斷的積累經驗,修正認知。 “陛下,臣欲往倭國。”熊廷弼看袁可立說完了,終于輪到自己了,他已經迫不及待了。 去倭國當然是殺倭寇,即便是東征九捷,大明完勝倭寇,但圍繞著礦區的小規模戰爭還在繼續,他前往倭國就是為陛下看好銀山。 “這么急的嗎?”朱翊鈞略有些不舍的說道:“要不還是去綏遠吧,綏遠現在道路通暢,若是有事,也方便回來。” 綏遠近,而且綏遠交通方便,回京坐著火車就回來了,現在去倭國,一年幾封信,幾年都見不到一次了。 而且倭國石見銀山也是個窮鄉僻壤的地方,要什么沒什么,去那邊就是吃苦。 “綏遠已經安穩了。”熊廷弼滿臉笑容的說道:“陛下,殿試之前,陛下和先生都以科舉為重,不讓臣出門,臣已經錯過了入朝抗倭,無論如何,都不能再錯過前往倭國的機會了,否則臣會懊悔終身。” 綏遠已經很安穩了,已然不用拼命了,去倭國可能會死,但不去,一輩子都會后悔。 就熊廷弼而言,他寧愿不考科舉,也想入朝抗倭,他其實還喜歡走武夫的路線,簡單而且直接。 “當謹記萬宗伯所言,夷狄狼面獸心,畏威而不懷德;還有那句,倭人有小禮而無大義,固擅下克上也。” “到了倭國,切記,不要相信任何的倭人,你這個年紀,還有些年少天真,總覺得有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但朕看來,人心隔肚皮,沒有翻臉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想法。” “全楚會館的老木匠梁叔梁壽堅,朕見過他好多次,完全沒想到他會這么做。” “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有活著,才能為大明盡忠。”朱翊鈞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手,雄鷹長大了要翱翔于天際之間。 “臣謹遵圣誨。”熊廷弼再俯首,他要去的地方是石見銀山,要做的事,就是擊退一切膽敢染指陛下銀礦的倭寇,這是利益之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溫情可言。 對于袁可立而言,梁壽堅的行為頂多是栽贓陷害。 但對于熊廷弼而言,他的書箱被放了夾帶,梁壽堅的行為是背叛,梁叔作為他成長經歷中極其重要的人,這種背叛,讓熊廷弼深切的明白了,人心隔肚皮是多么傷人。 熊廷弼也第一次理解了,為何陛下總是更喜歡把關系建立在利益上,而不是情感上,比如陛下對總督府的管理,就是利益為先,而非情感。 利益關系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鈞示意馮保取來了兩本書,讓馮保遞給了二人,笑著說道:“送你們一本書吧,這是王次輔的暢銷書《論五步蛇的自我修養》。” “額…”袁可立滿是錯愕,陛下的禮物居然是這本書,別說袁可立疑惑了,連熊廷弼都是眉頭緊蹙,顯然十分的意外。 熊廷弼非常不喜歡王崇古,這就是個奸臣,要不是萬歷元年之后,再無作奸犯科,早該上刑場的人了。 朱翊鈞語重心長的說道:“哎,人心里的成見就是一座大山。” “王次輔這本書要好好讀,這里面,都是做官的學問,是你們缺的東西,這可是海總憲推薦過的書,徐成楚也有一本,是海總憲贈送的,要對付敵人,要做的就是知己知彼。” “如果你對敵人不夠了解,又如何言勝呢?” “陛下圣明。”熊廷弼和袁可立互相看了一眼,滿是了然,原來是為了了解敵人! 那就必須要好好讀了,讀通透,讀明白,知道敵人所思所想,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王崇古是個奸臣不假,但王崇古不是個反賊,是否有那個心思,朱翊鈞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但王崇古的行為上,沒有走上反賊的道路,這是關鍵。 張四維安排人刺王殺駕的時候,王謙給張四維下毒,張四維找死,王家人可不想一起死。 王崇古早些年殺過倭寇,到了宣府大同,他雖然借著北虜發財,但從來沒有讓北虜犯境,而且自萬歷三年回京,領了工黨后,已經成為了大明的中流砥柱,國之柱石。 這也符合《自我修養》這本書的內容,奸臣是奸臣,反賊是反賊,奸臣是濁流,清流濁流,皇帝都要用,奸臣總是會自己找到出路。 奸臣做什么,很多時候,主要看皇帝的命令,因為奸臣的目的是升轉,而不是和反賊一樣顛覆大明。 朝中還公認,萬士和是個諂臣,不影響人家死后殊榮,也不影響皇帝陛下把萬士和掛在嘴邊。 袁可立回到全楚會館后,就打開了書開始看,第一遍看,他對里面的觀點嗤之以鼻,簡直是胡言亂語,要天下人都這樣,天下能好才怪。 他合上之后,又打開看了許久,他照著里面奸臣的標準,和自己的行為對比之后,發現無意間,奸臣竟是我自己! 簡直是簡直了,袁可立看完了《自我修養》,有些呆滯了起來。 奸臣的第一原則,崇上,上司的指示高于一切,無論如何要引起上司的注意,無論要贏得上司的認可,你做的一切,都要讓上司看到,否則就是白做; 圍繞著第一原則,有三個規矩。 第一,抓住一切和上司接觸的機會,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還要留下好印象; 第二,著力做出讓人肯定的成績,并且一定要讓上司了解其中艱難; 第三,做好總結,給上司留好功勞,宣傳上,一定要有上司英明領導; 想要升官,這一個原則三個規矩,就要熟練掌握,圍繞著萬歷維新的新形勢,王崇古也給出了新的辦法,因為考成法的推行,這三個規矩的權重也發生了變化,第二個規矩上升到首先遵循的規矩,即做出成績。 因為考成法,只要多數人認可的成績,那上司一定能看到這份成績。 而在上司詢問的時候,作為奸臣,一定要把困難告訴上司,大倒苦水,在一些旁支末梢的環節,要求助上司,給足上司參與感,這一點非常非常關鍵。 王崇古之所以要這么做,是王崇古入仕以來這么多年,他的頂頭上司,多數時候,都是一無是處的酒囊飯袋,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還會拖后腿,他入仕這么多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給上司的異想天開、一廂情愿擦屁股。 旁支末梢的地方,讓上司有參與感,大事方面,上司就沒有那么多興趣指手畫腳了,當事成之后,上司也可以合理的拿到一部分的功勞。 這就是王崇古的向上管理,他這么說,也這么做,但有的時候也會出問題,這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有的時候也會失效。 王崇古特別舉了個例子,比如皇宮中軸線鼎建,這可是天大的事兒,陛下蒞臨現場,講可以用建筑垃圾回填,講可以把未曾澆筑完全的水泥柱,用抹灰人,抹一遍灰了事,而不是拆了重建。 這件事,完全符合旁支末梢的部分,請陛下蒞臨指導。 但王崇古真的沒法干。 王崇古當初就很想大聲的告訴陛下,這是皇宮,皇宮!神器所在!皇帝是覺得反正沒有多高,而且也不重,完全足以支撐了,能省則省,總歸是塌不了。 這違反了自我修養的第一原則,崇上,上司的指示高于一切這一標準,王崇古沒那個膽子在皇宮鼎建上偷工減料。 如果能力不足,做不成事,又當如何? 王崇古的答案是,無能不要做奸臣,因為做奸臣要比忠臣更有才能,這樣上司才不舍得拋棄你,無能也不要做忠臣,因為你不比奸臣有才能,你的忠誠一文不值。 無能就是無能,回家種地才是最好的歸宿。 而袁可立會試答卷,就有點像是為了吸引陛下注意寫的,符合第一規矩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要留下好印象,毫無疑問,他給陛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當然這本書對袁可立而言,最大的收獲,是學到了狗斗術,無論是奸臣也好,忠臣也罷,都要會的技能,如果不會,輸了,你跟大局就沒有任何關系了。 張居正也是斗贏了,才一步步的走到了元輔的位置。 殿試很快就張榜了,皇帝沒有更改會試的排名,直接發榜,熊廷弼從會元變成了狀元,袁可立是榜眼,探花依舊是吳道南。 而在發榜當天,大明準備已久的《大明軍東征記》和《東征英豪錄》正式刊行了,之所以要這個時間刊行,完全是為了迎接大軍凱旋做準備,降階郊勞之禮在緊張的籌備中。 東征英豪錄里,有二十八星宿,比如婁虎駱尚志。 駱尚志原來是一個普通的農夫,浙江余姚駱家灣人,說是駱賓王之后,他是世襲百戶,衛所敗壞后務農為生。 他不是武舉出身,也不是捐納升遷,而是完全靠著天生神力,人送外號駱千斤,他的臂力驚人,能舉千斤,能開虎力弓十五箭,次日可再戰的悍勇之人。 從地方遴選入京營后,在萬歷九年就參加了討伐俺答汗之戰,而后在萬歷十三年入朝抗倭。 在東征九勝中,他打了八場,他作為京營把總出戰,本身卻是陷陣先登。 在平壤,他堵住了小西行長的退路,才導致小西行長被朝鮮花郎踩死; 在開城,他一手舉盾、一手持戟、攀云梯攻城,為第一先登; 在仁川、在漢城,他是馬山館爭奪戰的大功臣,斬倭寇物見隊百人,僅次于出身菜戶營的趙吉; 在忠州,他是打忠州山城的陷陣軍,九進九出,首級功二十七人; 在釜山,他率海防巡檢、墩臺遠侯二十七人,一人三馬,一晝夜長途跋涉二百四十里,打的倭寇措手不及; 在蔚山,披堅執銳、身先士卒,被倭寇投石所中,依舊力戰奪城; 在對馬,他率先攻入邪馬臺軍港,配合陳天德,拿下邪馬臺山城; 在長門,他奇兵埋伏毛利輝元,斬毛利輝元領兵大將村上武吉,這是毛利家水師的最高軍團長,更是一切倭寇的源頭。 除了京都之戰,他沒有參與之外,其余都是死戰不退。 陳天德作為大明軍瞭山,也榜上有名,為南天朱雀之首井宿,他的功績主要涉及到了情報方面的支持。 禮記·曲禮有云: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 意思就是軍陣就像是天上的星宿一樣,朱雀七宿都和斥候、情報有關;而玄武主要和后勤、物資保證有關;青龍為中軍,而白虎主殺伐,主要負責攻堅。 所以駱尚志為婁虎,陳天德為井雀,趙吉是奎虎,為西天白虎之首奎宿。 李如松為角龍,為東天青龍之首角宿,而作戰英勇一樣英勇的副總兵馬林,為亢龍,為東天青龍第二。 至于戚繼光,他是奉國公,如果硬要給他弄個星官,他也是太微垣里的上將星,或者北斗七星里的破軍。 禮部可沒有糊弄皇帝的意思,真的在好好的宣傳,東征九勝里涌現出的各種英豪。 大明贏學在穩步構建之中。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八百六十八章 利益關系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鈞雖然把兗州孔府的根兒都拔了,但他其實不反對儒學,甚至覺得孔子、孟子,很多四書五經講的很有道理。 即便是萬歷維新浩浩蕩蕩,大明的丁亥學制,并沒有拋棄儒學,因為儒學里面有很多的內容,也是值得借鑒的,無論是個人的修身,還是國朝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比如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也就是朱翊鈞所說的,國朝最為危險的就是鮮花錦簇日,歌舞升平時。 如果沒有任何的危機意識,國家滅亡就是必然的,作為統治階級,不能沉湎于鮮花錦簇和歌舞升平,而是應該看到水面下暗流涌動的危機。 因為一旦沉湎于鮮花錦簇和歌舞升平,就必然會帶來一個可怕的結果,那就是飾勝,把一切的一切都包裝成為勝利,輸也能變成贏,最終在不斷的贏贏贏的掌聲中,走向滅亡。 大明在晚明到南明這段時間,就充斥著這種贏贏贏的風潮,闖王李自成被剿滅了數次,最慘烈的時候,身邊就只有二十一人,但很快他就再次拉起了百萬的農民軍,把大明王朝給斷了。 崇禎九年,第一代闖王高迎祥被剿滅,高迎祥被拉到京師凌遲處死,這對大明而言是巨大的勝利,從萬歷末年開始的陜甘寧三地的民亂,看似是畫上了一個句號。 崇禎皇帝贏了,但其實也沒有真正的勝利,因為他沒有解決民亂爆發的根本誘因。 朝廷欠餉,讓三邊軍屯衛所的基層軍官都開始逃離衛所,加入了農民軍成為了基層的組織者,讓農民軍有了正面對抗官軍的實力; 其次,陜甘寧三邊大旱,沒有糧食賑濟災民,無窮無盡走投無路的百姓,只能跟隨闖王。 最重要的還是人地矛盾,自萬歷十年張居正離世后,天下再無人敢抑制兼并,因為地主官僚階級對張居正為首的張黨,展開了最深入的清算,任何和張居正有一點關系的人,都要被徹底打倒,地主官僚階級勝利了,再沒人敢抑制兼并了。 消滅農民軍對于大明官軍而言不是難事,一直到崇禎十五年,大明官軍對農民軍依舊是優勢,洪承疇對農民軍幾乎完勝,但贏,已經沒什么用了,可是如何讓百姓安頓下來,不再成為農民軍的兵源,才是最大的矛盾。 而矛盾說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觀察問題的方法論,現象、問題、原因、方案、實踐、修正、再推行、再修正,這一套的方法論,無往不利。 大明贏學要真的贏,要建立在矛盾說的基礎上、建立在華夷之辯的基礎上,而不是飾勝。 大明士大夫普遍可以接受在陽明心學上建立的矛盾說,也可以接受在華夷之辯、矛盾說上建立的大明贏學,而不是蠻夷飾勝贏學。 但大明士大夫階級,其實真的很難以接受階級論。 大明士大夫在大明思辨成果文集的傳播過程中,對矛盾說的注釋進行自己注解,但對階級論則采用刪減、修改的方法,來對抗階級論的傳播。 在許多讀書人的眼里,矛盾說很好,甚至值得深入討論,可階級論得看統治者是否認可。 張居正寫出第二卷分配,就直接燒了,不是皇帝挽救及時,根本不會刊行。 而階級論第三卷干脆就是朱翊鈞寫的了,連張居正這個革故鼎新的改革家、變法者,都難以接受第二卷,更別說第三卷了。 朱翊鈞和袁可立伸出了同樣的手,就是告訴袁可立,他的立場,他們在志向上相同,在行為上相同,在階級認同上相同,同志同行則同樂者。 “陸樹聲到全楚會館索人,朕不認可,他自己選擇私門小利,以個人利益為首,那是他的自由,自私在朕看來,是個中性的詞,人不自私,那就不是人了。”朱翊鈞頗為確切地說道:“但他不能以自己的行為標準,去要求別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兒,也不要強加于他人,這句話強調的是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的那套利己思維,強加于別人身上,這才是有修養,人和人各有不同。 “先生主要是擔心袁可立沒有人給他撐腰,扛不住一些風波。”熊廷弼為張居正說了句好話,殿試之后,單獨宣見了兩名學子,這是告訴天下人,袁可立是皇帝罩著,可之前袁可立可沒這等殊榮。 人要活在現實里,自己承擔不了的風波,要極力去避免,那不是迎難而上,而是找死。 “現在有人給禮卿撐腰了。”朱翊鈞當然清楚張居正的擔心,怕百年之后,袁可立還沒成長起來,沒有保護自己的力量。 拜師陸樹聲,做個看起來有點傳統的讀書人,對于袁可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否則他就不會罵萬歷皇帝了,還罵的那么難聽。 朱翊鈞看著袁可立說道:“禮卿會試的文章,朕看了,你的文章寫的很好,六千舉人,只有七十份說了這萬歷維新的弊端。” 袁可立在歌功頌德和針砭時事上選擇了后者,他其實早就做出了選擇,而不是陸樹聲上門,才做了選擇。 貢院會試多了一個規矩,因為是皇帝發考籃,所以所有的草稿紙張,不得帶出考場、不準丟棄,而緹騎會將每一張草稿紙收集起來,對每一名中式貢士進行核驗,防止弄虛作假。 搜檢懷挾官仍然常設,因為有些人會把夾帶藏進谷道里,雖然非常惡心,但確實發生過,這塞進谷道里,總不能是有人栽贓嫁禍了。 在搜檢之外,現在會試,多了一套驗證的程序,沒有人的文章是一氣呵成的,尤其是這會試,需要多次謄抄,力求寫到完美,那么草稿紙,就成為了核驗的重要工具。 等到確定無誤后,這些草稿紙會被打碎放入池子中,放入白土漂白后,再次做成紙張。 浪費是極其可恥的。 因為有核驗的程序,所以袁可立寫了一篇錦繡文章,修改好了,最終卻選擇了針砭時事,這是勇氣。 而袁可立的文章寫的極好,主要是萬歷維新的新政,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新政在河南地方是非常成功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 袁可立從河南本身出發,探討了內陸地區的發展困境。 大明已經形成了一種路徑上的依賴,大明貧銀貧銅、內部貨幣錢荒、內部需求不足、海外有金銀銅、產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大規模生產用商品換到貴金屬、再投入擴大再生產、而后逐步輻射腹地。 這種路徑有兩個巨大的弊病。 第一個生產再擴大仍然在滿足外部需求,而非內部,甚至因為外部需求不夠旺盛,陷入了惡性競爭的困局之中,擴大后的生產,并沒有逐步輻射到腹地。 造成這種原因也簡單,內地的錢荒問題,沒有根本性改變; 這個弊病是極為可怕的,因為無法完成內需的建設,大明空有商品優勢,完全無法發揮商品經濟的優勢,從海貿中,獲取更多超額的利潤的同時,還會增加離心力。 價值受勞動強度、勞動時間、勞動難度影響,而價格圍繞著價值、供需、成本進行波動,這是生產圖說里關于價值和價格的討論。 大明沿海地區產業豐富,大明內部無法消化,就得依靠外部需求,這個時候,主動權就交給對方。 這就走入了一個怪圈,產業越豐富,越密集,越要壓價,利潤降低,越不賺錢的困境。 大明是個整體,但兩京一十五省五大總督府,也有個嫡庶之分,在重大危機面前,還有可能各地趨同,可是涉及到了各種細分的產業利益瓜分,親兄弟也要明算賬的。 如何在萬歷維新中,保證向心力,不因為利益分配的問題分家,是朝廷必須要考慮清楚的。 簡單而言,就是外向型經濟,造成的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內需建設不充分導致內需不足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影響國朝根本。 第二個問題,就是老生常談的人口流失、人口不足的問題了,而袁可立用一句俗語,解釋了這個現象背后折射的問題:窮的不生,中人之家也不生; 原因也簡單:干活的時候嫌人少,吃飯的時候嫌人多。 窮是討不到媳婦,就是討得到,生出來養不起,所以不生,但中人之家,也不生,就非常詭異了,大明很多的中人之家,即便是有了孩子也會溺死,不是養不起,而是供不起。 大明天下,窮人和中人之家占據了絕對的多數,他們不生,大富大貴、頂層向下開枝散葉,又能生幾個?王崇古家里足夠有錢,他就兩個兒子,還有一個英年早逝,留下一個王謙,而王謙一共就兩個兒子,兩個閨女,說什么也不肯生了。 而袁可立在會試的文章里分析了問題的癥結。 小到一個家庭,大到大明江山,都是如此。 干活的時候,希望人多多的,一起創造財富,等到分配的時候,又開始嫌吃飯的人多,即便在鄉野之間,耕種農桑最需要勞力,可是一個勞力從小到大,吃的又多了。 袁可立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談,絲毫沒有露出任何怯懦,將自己的想法解釋的非常清楚。 對第一個問題,他提出了三個主要解決的辦法,大建馳道進行分配、黃河歸故讓兩淮地區擺脫黃河帶來的困擾、而后疏浚淮河、長江,讓沿海的富裕順著大江大河馳道,向腹地輻射。 當然這都是遠景規劃,現在大明的生產力,還是對黃河有些無能為力,讓黃河歸故才能疏浚淮河,讓長江黃河流域,輻射到大明大部分地區,沒有大江大河的地方,則依托于馳道。 這個思路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時間尺度在百年之上。 第二個問題,則主要聚焦于田政之上,清丈還田、營莊減租,四管齊下,期許在有生之年,能夠徹底執行下去,最終奠定了萬歷盛世的堅實根基。 相比較還田,袁可立更加推崇營莊法。 在他看來,還田之后,這些田土最后還是會被兼并,營莊集體所有,反而會讓鄉野之間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大富大貴不敢想,但吃得上飯還是可以期許的。 朱翊鈞叫袁可立入通和宮,其實沒什么正事,就是一種立場宣示,他就是個學生,經驗不足,討論的內容,十分的空洞,他需要不斷的成長,在實踐中不斷的積累經驗,修正認知。 “陛下,臣欲往倭國。”熊廷弼看袁可立說完了,終于輪到自己了,他已經迫不及待了。 去倭國當然是殺倭寇,即便是東征九捷,大明完勝倭寇,但圍繞著礦區的小規模戰爭還在繼續,他前往倭國就是為陛下看好銀山。 “這么急的嗎?”朱翊鈞略有些不舍的說道:“要不還是去綏遠吧,綏遠現在道路通暢,若是有事,也方便回來。” 綏遠近,而且綏遠交通方便,回京坐著火車就回來了,現在去倭國,一年幾封信,幾年都見不到一次了。 而且倭國石見銀山也是個窮鄉僻壤的地方,要什么沒什么,去那邊就是吃苦。 “綏遠已經安穩了。”熊廷弼滿臉笑容的說道:“陛下,殿試之前,陛下和先生都以科舉為重,不讓臣出門,臣已經錯過了入朝抗倭,無論如何,都不能再錯過前往倭國的機會了,否則臣會懊悔終身。” 綏遠已經很安穩了,已然不用拼命了,去倭國可能會死,但不去,一輩子都會后悔。 就熊廷弼而言,他寧愿不考科舉,也想入朝抗倭,他其實還喜歡走武夫的路線,簡單而且直接。 “當謹記萬宗伯所言,夷狄狼面獸心,畏威而不懷德;還有那句,倭人有小禮而無大義,固擅下克上也。” “到了倭國,切記,不要相信任何的倭人,你這個年紀,還有些年少天真,總覺得有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但朕看來,人心隔肚皮,沒有翻臉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想法。” “全楚會館的老木匠梁叔梁壽堅,朕見過他好多次,完全沒想到他會這么做。” “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有活著,才能為大明盡忠。”朱翊鈞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手,雄鷹長大了要翱翔于天際之間。 “臣謹遵圣誨。”熊廷弼再俯首,他要去的地方是石見銀山,要做的事,就是擊退一切膽敢染指陛下銀礦的倭寇,這是利益之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溫情可言。 對于袁可立而言,梁壽堅的行為頂多是栽贓陷害。 但對于熊廷弼而言,他的書箱被放了夾帶,梁壽堅的行為是背叛,梁叔作為他成長經歷中極其重要的人,這種背叛,讓熊廷弼深切的明白了,人心隔肚皮是多么傷人。 熊廷弼也第一次理解了,為何陛下總是更喜歡把關系建立在利益上,而不是情感上,比如陛下對總督府的管理,就是利益為先,而非情感。 利益關系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鈞示意馮保取來了兩本書,讓馮保遞給了二人,笑著說道:“送你們一本書吧,這是王次輔的暢銷書《論五步蛇的自我修養》。” “額…”袁可立滿是錯愕,陛下的禮物居然是這本書,別說袁可立疑惑了,連熊廷弼都是眉頭緊蹙,顯然十分的意外。 熊廷弼非常不喜歡王崇古,這就是個奸臣,要不是萬歷元年之后,再無作奸犯科,早該上刑場的人了。 朱翊鈞語重心長的說道:“哎,人心里的成見就是一座大山。” “王次輔這本書要好好讀,這里面,都是做官的學問,是你們缺的東西,這可是海總憲推薦過的書,徐成楚也有一本,是海總憲贈送的,要對付敵人,要做的就是知己知彼。” “如果你對敵人不夠了解,又如何言勝呢?” “陛下圣明。”熊廷弼和袁可立互相看了一眼,滿是了然,原來是為了了解敵人! 那就必須要好好讀了,讀通透,讀明白,知道敵人所思所想,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王崇古是個奸臣不假,但王崇古不是個反賊,是否有那個心思,朱翊鈞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但王崇古的行為上,沒有走上反賊的道路,這是關鍵。 張四維安排人刺王殺駕的時候,王謙給張四維下毒,張四維找死,王家人可不想一起死。 王崇古早些年殺過倭寇,到了宣府大同,他雖然借著北虜發財,但從來沒有讓北虜犯境,而且自萬歷三年回京,領了工黨后,已經成為了大明的中流砥柱,國之柱石。 這也符合《自我修養》這本書的內容,奸臣是奸臣,反賊是反賊,奸臣是濁流,清流濁流,皇帝都要用,奸臣總是會自己找到出路。 奸臣做什么,很多時候,主要看皇帝的命令,因為奸臣的目的是升轉,而不是和反賊一樣顛覆大明。 朝中還公認,萬士和是個諂臣,不影響人家死后殊榮,也不影響皇帝陛下把萬士和掛在嘴邊。 袁可立回到全楚會館后,就打開了書開始看,第一遍看,他對里面的觀點嗤之以鼻,簡直是胡言亂語,要天下人都這樣,天下能好才怪。 他合上之后,又打開看了許久,他照著里面奸臣的標準,和自己的行為對比之后,發現無意間,奸臣竟是我自己! 簡直是簡直了,袁可立看完了《自我修養》,有些呆滯了起來。 奸臣的第一原則,崇上,上司的指示高于一切,無論如何要引起上司的注意,無論要贏得上司的認可,你做的一切,都要讓上司看到,否則就是白做; 圍繞著第一原則,有三個規矩。 第一,抓住一切和上司接觸的機會,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還要留下好印象; 第二,著力做出讓人肯定的成績,并且一定要讓上司了解其中艱難; 第三,做好總結,給上司留好功勞,宣傳上,一定要有上司英明領導; 想要升官,這一個原則三個規矩,就要熟練掌握,圍繞著萬歷維新的新形勢,王崇古也給出了新的辦法,因為考成法的推行,這三個規矩的權重也發生了變化,第二個規矩上升到首先遵循的規矩,即做出成績。 因為考成法,只要多數人認可的成績,那上司一定能看到這份成績。 而在上司詢問的時候,作為奸臣,一定要把困難告訴上司,大倒苦水,在一些旁支末梢的環節,要求助上司,給足上司參與感,這一點非常非常關鍵。 王崇古之所以要這么做,是王崇古入仕以來這么多年,他的頂頭上司,多數時候,都是一無是處的酒囊飯袋,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還會拖后腿,他入仕這么多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給上司的異想天開、一廂情愿擦屁股。 旁支末梢的地方,讓上司有參與感,大事方面,上司就沒有那么多興趣指手畫腳了,當事成之后,上司也可以合理的拿到一部分的功勞。 這就是王崇古的向上管理,他這么說,也這么做,但有的時候也會出問題,這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有的時候也會失效。 王崇古特別舉了個例子,比如皇宮中軸線鼎建,這可是天大的事兒,陛下蒞臨現場,講可以用建筑垃圾回填,講可以把未曾澆筑完全的水泥柱,用抹灰人,抹一遍灰了事,而不是拆了重建。 這件事,完全符合旁支末梢的部分,請陛下蒞臨指導。 但王崇古真的沒法干。 王崇古當初就很想大聲的告訴陛下,這是皇宮,皇宮!神器所在!皇帝是覺得反正沒有多高,而且也不重,完全足以支撐了,能省則省,總歸是塌不了。 這違反了自我修養的第一原則,崇上,上司的指示高于一切這一標準,王崇古沒那個膽子在皇宮鼎建上偷工減料。 如果能力不足,做不成事,又當如何? 王崇古的答案是,無能不要做奸臣,因為做奸臣要比忠臣更有才能,這樣上司才不舍得拋棄你,無能也不要做忠臣,因為你不比奸臣有才能,你的忠誠一文不值。 無能就是無能,回家種地才是最好的歸宿。 而袁可立會試答卷,就有點像是為了吸引陛下注意寫的,符合第一規矩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要留下好印象,毫無疑問,他給陛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當然這本書對袁可立而言,最大的收獲,是學到了狗斗術,無論是奸臣也好,忠臣也罷,都要會的技能,如果不會,輸了,你跟大局就沒有任何關系了。 張居正也是斗贏了,才一步步的走到了元輔的位置。 殿試很快就張榜了,皇帝沒有更改會試的排名,直接發榜,熊廷弼從會元變成了狀元,袁可立是榜眼,探花依舊是吳道南。 而在發榜當天,大明準備已久的《大明軍東征記》和《東征英豪錄》正式刊行了,之所以要這個時間刊行,完全是為了迎接大軍凱旋做準備,降階郊勞之禮在緊張的籌備中。 東征英豪錄里,有二十八星宿,比如婁虎駱尚志。 駱尚志原來是一個普通的農夫,浙江余姚駱家灣人,說是駱賓王之后,他是世襲百戶,衛所敗壞后務農為生。 他不是武舉出身,也不是捐納升遷,而是完全靠著天生神力,人送外號駱千斤,他的臂力驚人,能舉千斤,能開虎力弓十五箭,次日可再戰的悍勇之人。 從地方遴選入京營后,在萬歷九年就參加了討伐俺答汗之戰,而后在萬歷十三年入朝抗倭。 在東征九勝中,他打了八場,他作為京營把總出戰,本身卻是陷陣先登。 在平壤,他堵住了小西行長的退路,才導致小西行長被朝鮮花郎踩死; 在開城,他一手舉盾、一手持戟、攀云梯攻城,為第一先登; 在仁川、在漢城,他是馬山館爭奪戰的大功臣,斬倭寇物見隊百人,僅次于出身菜戶營的趙吉; 在忠州,他是打忠州山城的陷陣軍,九進九出,首級功二十七人; 在釜山,他率海防巡檢、墩臺遠侯二十七人,一人三馬,一晝夜長途跋涉二百四十里,打的倭寇措手不及; 在蔚山,披堅執銳、身先士卒,被倭寇投石所中,依舊力戰奪城; 在對馬,他率先攻入邪馬臺軍港,配合陳天德,拿下邪馬臺山城; 在長門,他奇兵埋伏毛利輝元,斬毛利輝元領兵大將村上武吉,這是毛利家水師的最高軍團長,更是一切倭寇的源頭。 除了京都之戰,他沒有參與之外,其余都是死戰不退。 陳天德作為大明軍瞭山,也榜上有名,為南天朱雀之首井宿,他的功績主要涉及到了情報方面的支持。 禮記·曲禮有云: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 意思就是軍陣就像是天上的星宿一樣,朱雀七宿都和斥候、情報有關;而玄武主要和后勤、物資保證有關;青龍為中軍,而白虎主殺伐,主要負責攻堅。 所以駱尚志為婁虎,陳天德為井雀,趙吉是奎虎,為西天白虎之首奎宿。 李如松為角龍,為東天青龍之首角宿,而作戰英勇一樣英勇的副總兵馬林,為亢龍,為東天青龍第二。 至于戚繼光,他是奉國公,如果硬要給他弄個星官,他也是太微垣里的上將星,或者北斗七星里的破軍。 禮部可沒有糊弄皇帝的意思,真的在好好的宣傳,東征九勝里涌現出的各種英豪。 大明贏學在穩步構建之中。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八百六十八章 利益關系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休閑文學吧提供免費小說,請讀者支持正版